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阅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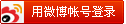
x
赫鲁伯谈话录|“我怎么能闭嘴,我还从没开始说话呢”

捷克医学家诗人米洛斯拉夫·赫鲁伯(Miroslav Holub,1923.9.13-1998.7.14)捷克著名诗人、作家,同时他是布拉格医学院一位著名的免疫学专家。1923年,他出生于捷克西波西米亚(Western Bohemia)的普勒扎(Plzen),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一名中学的德文和法文教师,从小赫鲁伯就深深地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在二战结束之后,也就是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写作,并同时在医学上有所建树。
在他人生的最后30年里,他在 诗歌领域和医学领域同时获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成为一位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的免疫学专家,1967年,他的第一本英文诗集出版,从此他的诗作引起了世界的好奇,在大西洋两岸颇有反响,曾经获得意大利费拉亚诺(Flaian o) 诗歌奖(中国诗人杨炼曾经在1999年获得该奖项)。
赫鲁伯一生发表超过140篇科学论文,出版3本科学专著,出版了14本诗集,5本 散文集。在西方,他和以色列诗人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波兰诗人 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并称“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三大诗人”。曾经一段时期,因为受到政治迫害,他的随笔只能匿名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不过即便这样,他独特的风格还是被细心的读者辨认了出来。 译|唐浩
一
[提问者:Chris Kennedy , Michael P. Thomas]
经历了高压政治制度里的生活,如今身处一个“自由社会”,你的写作是否有了某种程度的转变,而政治气候是否会影响作家创作的品质或者风格? 赫鲁伯:毫无疑问,政治气候有一种深刻的影响,不在风格上,而在传递的信息上,在作品的内容上。八九变革之后,有很多诗人和散文作者失败了,因为他们的写作主题不够用了。原本的主题是反抗苏联对捷克生活的压制,或者为了有尊严的人类生活而反抗巨大的谎言,但突然间它消失了。我觉得,人们应该表现,文学应该表现每个人的宽慰心情,但令我惊讶的是,并非如此。个体的抱怨变成了整体的抱怨,但我确实认为人们应该换成一种乐观的语调。这次我的经验总结是,有些东西在现代文学里深深建构了,它们对整体状况的态度是黑色的,悲观的,或者是酸腐的。年轻一代眼中的景象是漆黑一片,相比之下,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反倒积极得多。另一方面,我的规划并不会改变,因为我的动因是反对愚昧,反对等级制度。在政治变局之后,我立即有了新的动因,因为我看见了新的迷信。知识生活的第一个变化是乞灵于另类的医学、科学和文化。所有东方的观念都从他们的魔瓶里倒了出来。早在最初的那些年,我们周围就有很多玄奥的形而上学,禅宗信徒,东方精神导师的书籍和文本。商业印度导师拜访我们,搭起帐篷,向穷人宣道而牟取暴利。我觉得,在我们的环境里,在我们文明化的国家里,这类迷信实在太多了,我不会失去我的动因。我会和各种面目的同一种愚昧、同一种荒谬的人类状态斗争下去。 你认为写作时找某些东西去反对是人类的天性吗? 赫鲁伯:有时我注意到,我是少数坚定支持新政治体制的人之一。这么多人——知识分子们——对眼下文化缺少支援感到失望。诗集的印数从2000本到500本到无人阅读,很少人会买严肃文学作品,但我不会抗议,因为这是自由的部分代价。一个基本的问题, 我们应该有一个剥夺我们做人尊严的,却能提高文学兴趣的极权制度呢,还是说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是我们的第一义务?我的答案当然是后者。生活是首要的,文学是次要的。我欢欣雀跃,我也想在我的作品里表现,我们重建了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现在是正常的欧洲人,不再是贫困的捷克人,而这就是一切。如今我获得了人的满足感和人的希望感,我真的可以让它入诗。每一首现代诗都有某种引力,使人进入黑暗,进入不确定,进入相对主义。你的感觉就像被诗里的一股强迫性的重力驱赶,引向某地,进入小小的私家地狱或者小小的私家炼狱,却从来不是小小的私家天堂。这总让我想起一则古老的捷克笑话,有个小男孩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有一天吃午饭他突然猛敲汤勺,然后说“汤不够咸,我不喝了。”他的妈妈说,“别急,盐在这里,但为什么你从不吭声,突然间对汤发表意见了?”男孩说,“嗯,因为以前的汤还行。” 所以,既然汤还行,为什么我们就该说话,或者为什么我们就该有文学。 如果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在免疫学家和诗人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在人类尊严的领域和文学之间,你的工作会倾向于前者吗?作为一名科学家,你的工作会在这个领域做得更深入一些吗? 赫鲁伯:很有趣,你提到了人类尊严,或许我从未说过,但科学可能不得不面对人类尊严,而不只是死抱着一些废话,仿佛它们是某种混凝土,能立即填进科学的星际网络,尤其今天,有各种信息高速公路,有各种科学世界的互联通道。有些东西令到我们在实验室的具体工作里不再像扮演小丑的角色,当我们探讨我们的情感等等东西时,我们也不再只是搬弄词汇。我的感觉是,在科学里,我们可以说我们至少有了重要的东西去发挥才智。我们学会了提出重要的问题。在艺术和人文学科,我从来不能确定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在艺术和人文学科里,我们拥有的答案要比问题多。 你表达的是向前推动你的最佳自我。如果一个人可以有最佳的自我,一个诗人也是如此吗? 赫鲁伯:出于本能,我不喜欢“最佳”。我只会说“较佳”。 较佳的自我? 赫鲁伯:较佳的自我。有时,特别是情绪糟透了的时候,我们的有些作家会呈现他们最坏的自我,有时那些看起来绝对悲观避世的作家反倒不会。他们只是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想让自己显得更有趣吗?我不知道缘由。 你的许多诗,像“关于精确性的简短沉思”和“还有什么”,我觉得非常幽默。你是不是觉得诗歌遗忘了幽默。 赫鲁伯:经常遗忘。当然,捷克有这样的天才,擅长某种佯谬的反讽或者某种内敛的幽默。但我想说,整体而言它确实被压抑了。对我来说,幽默或反讽或笑是第一美学范畴的。因为我发现,在写作和阅读中,它是一个人能获得的最好的回应。面对一首严肃的诗,人们至多是倾听,或者睡着了。面对一首好玩的诗,他们微笑,显示出人类的休戚关系,人类的互相理解,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因此我会尽可能地幽默,前提是它仍然是诗。有时我会运用超现实的意象,运用我自己的想象力,这当然受到了以前一些超现实主义者的影响,仅仅因为它好玩。我们有一位非常瞩目的年轻作家,他是一名硬核超现实主义者,我觉得耳目一新,因为他的超现实意象纯粹是好玩。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你觉得幽默能很好地被翻译吗?在翻译中,诗歌那一种品质不会丢失? 赫鲁伯:是的,毫无疑问,幽默不会在翻译中丢失。如果失去了幽默或反讽,说明翻译失败了。这是在其他语言里较易留存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不是那种诗人,非要译本和原来的一样。你不可能呈现同样的诗,因为诗歌不是书写的文本,而是感觉的文本。即使是最理想的翻译,可以传递所有东西,从音乐到暗示,到思想,到意象——即使是这样的译本,在布拉格、柏林或者锡拉丘兹,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方式。死抱着这样的想法——翻译必须信、达等等,是毫无意义的。我想要的是另一个版本的好诗。如果我的双关语或反讽无法翻译,那就换成当地的双关语或当地的反讽。当我和大卫·扬合作时,如果我粗略翻译后,他在译本里辨认不出好玩的那一句,我会在旁边注明,这里应该是好玩的。还是换成别的吧,我告诉他,用一些美国的俚语黑话。 在文选《另一个共和国》的导言中,编者查尔斯·西密克和马克·斯特兰德说,你的脉搏是“历史的”。他们列举了其他诗人阿米亥、里索斯、米沃什作为历史的,反对神话的。你的诗里有历史的脉搏吗? 赫鲁伯:这可能有点误解了。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解释阿米亥。我会说赫伯特也许可以贴上“历史的”标签。我们都经历了“凝重的历史”。在这意义上,我们在诗里可能倾向于有更多历史的暗示,而且基本上,这是建立在历史上的思维。这也是能意识到自己变化的思维,意识到我们做的每件事的历史根源。“历史的”并不意味着随时都在记录,但在它里面我们能感觉到流动和变迁,而在这意义上我们可能是“历史的”。但我发现这句子有点误解了,因为神话内藏于经验历史之中,因此没有全然的历史,也没有全然的神话。我认为“神话的”就是诗人抱着个人神话不放。我给这一流派贴的标签是“通灵的诗歌思维”,而另一流派是“沉静的诗歌思维”。我相当确定,我对描述过程感兴趣,而不是我的精神状态,我的激情,或者其他什么。写诗的时候,我清楚意识到时间的流逝,这一天,这一年,等等。我想,与东方的神话和东方的思维方式比较,这是西方的态度——意识到向前发展的不可逆、不复返。 我认为你的诗某种意义上是兼容并蓄的,你的语言、主题、材质甚至诗歌策略都趋向一个宽广的范围,涵盖了科学、历史和神话故事。有没有诗歌不该包容的,诗歌对于什么不能入诗有没有限制? 赫鲁伯:我们已知的所有诗歌方法包含了一切,倘若它够典型,或者说它依然是诗的话。诗歌的唯一限制就是诗歌。此外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如果一首诗是关于代数函项的,我看到了,我仍然会把它当成一首诗来读,前提是它有一些构成要素,或者阅读时它会提供一些传统的诗感。所以我不认为有太多类型的诗歌会受到排斥。 我最不喜欢的问题是“你的诗是关于什么的?”诗歌关于一切。赶快把你的目光投向宇宙世界吧。十九世纪的爱情诗和自然诗概念,我现在认为是荒谬的。即使你写一首现代爱情诗,它也蕴含了一切。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我写过一首诗叫“论下午六点的起源”,因为我在英格兰被定义成“布拉格的一名穷作家”,所以它引起一篇发表在《监护者》上的文章提出疑问,“赫鲁伯怎么了?它到底在说什么?”除了爱,它什么也没说。但因为它比较宽泛,不只是写眼睛、心灵和肉体,所以它可能会被误解成政治诗,其实它不是。 你认为必须面对东欧诗人表达的西方观点吗?你认为“东欧感受”存在吗,如果存在,它是什么? 赫鲁伯:如果是指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经历的“凝重的历史”,它是存在的。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英国诗人和我们的某类诗人有亲和关系,他们有某种相同的经验,区别不大,因为历史在西方有点渐渐地被冲淡了。英国人唯一错过的是这种体制。经历这种政治体制,或好或坏。而我们有凝缩的经验。基本上,我不认为这类动物学的标签能说得通,“东欧诗人”和“西欧诗人”。这种分类已经不存在了。 你知道,文学乐于混杂。米兰·昆德拉,他起初是诗人,然后是剧作家和小说家。在当代法国小说里,他的作品是极少数,极混杂的。还有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生活在多伦多的捷克小说家,他基本上往返于多伦多、布拉格两地,但他带着他深切的五六十年代的捷克经验,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加拿大作家。你能看见许许多多的混血儿。东欧或西欧已没有多少生物学的意义了,但愿如此吧。 以昆德拉为例,他必定和早期的法国文学有渊源关系。有没有什么可以显示你受了哪一类型的影响呢,或者你觉得受自己国家的作家影响更大吗? 赫鲁伯:不,毫无疑问,相比之下我受英美作品的影响更大。尽管我最初所受的影响来自法国。捷克诗人卡瑞尔·恰佩克译介了许多法国诗人。他也是剧作家和小说家。如果不是早早就在1938年去世,他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他年轻时有不少优美的译作,20世纪诗人兰波、瓦雷里等等。对于我,随后的一代也有非常出色的译者,雅克·普莱维尔,法国超现实主义者,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出于莫名而久远的理由,就像我所在的城市被一支美国军队解放了——我第一眼看见的外国人是美国人。加上我正好进入科学领域,而我们的国际语言是英语。我的感觉是,随后的岁月里,英语和美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捷克文化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受美国艺术家和诗人的影响更深一些。我们有这么多英文诗集或美国诗歌。但今天这些范本又换成了法文的了。我记得在89年,我们所理解的法国诗人,离我们的感受比较远,有点太过抽象,有点太过自我中心。然后突然出现了一大堆法国诗,一夜之间。随着政治变革,有相当数量的文学突然间充斥着某种法国腔。尽管他们大多数不会说法语。不过,我依然相信,一个较原始的想法 ,一个人始终受他所说的语言影响。 我非常确定,我的捷克文法受到了我说的德语、英语甚至是法语的影响。非常独出心裁的捷克诗人是那些不懂其他语言的诗人。如果懂其他语言,他们会被稀释,但这些捷克诗人,他们能深入到语言学里面。所以我们各有所失。但所失也不少,因为人类的大脑仍受制于它的功能。我想把这个写进一首新诗,“如果人类大脑的所有潜能都能真正运行,那么在下一个三百万年,我们每一秒都需要有一些新的信息。”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尽大脑的容量。这是乐观的信息,我会尽量把它写成更乐观的诗。 你谈起过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沉默时期,我觉得奇怪,它是如何影响你的工作的? 赫鲁伯:通常说来,我认为沉默是必需的。我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说,诗歌应尽可能用最少的词语,这是我的原话,但我仍然坚持它。前提是这些词语能产生适当的静默。我写过,我很吃惊,现代作家有如此高的词语生产能力。有时我觉得他们本能地喜欢雄性山鸟。他们不停地说,不停地说,就是停不下来。有一次我在澳州南部遇见三个说话作家,他们的交谈就是各自进行文学独白,他们说话如此急促,当我们下水游泳,他们几乎被淹死了。一位伟大的犹太作家最近到布拉格访问时说,“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说了这么多,也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听得这么少。”在喋喋不休里,我们远离了真正的倾听。在喋喋不休里,我们干扰了句子之间的沉默,字词之间的沉默,诗歌之间的沉默。因此对我而言,沉默是目标,真正的人类的沉默,不是喑哑,是沉默,内心的沉默充满了某种东西,我希望我知道它是什么。而它是一片沉默,如同一片富饶的土地。 有五年时间你停止了写作。对于你,那是什么样的日子? 赫鲁伯:是的,我有阻滞,那是在五十年代,原因很简单,没有诗的想象力。不管怎样,非党员不允许发表作品。但你还是无法在这种人类条件下想象诗歌。在极端的情形下,你知道政治谋杀在进行,当这些东西在进行,一个人怎么能写作呢?你觉察到了,但你不能说,因此只好闭嘴。 赫鲁伯:是的,毫无疑问,我写过一系列的散文诗对抗空虚。毫无疑问沉默不是空虚,沉默可以填充空虚。 1970年至1982年,你没出版任何东西? 所以这和你早期的沉默有所不同? 赫鲁伯:早期更痛苦,因为我的诗友和导师会告诉我,“米洛斯拉夫,这不是写诗的年代,这是我们展示沉默的年代。”而我会回答,“可是我怎么能闭嘴,我还从没开始说话呢。” 七十年代我成了无名氏,但这个时期我也硕果累累。首先,作为一个无名氏,我不会被任何电视、电台、通信打扰;我根本不存在。另外,我生活在捷克共和国,开了一个没署名的专栏。这些专栏文章编成了两本书,会在英国出版。因为我的散文风格非常特异,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专栏是我的。 《特别护理》里的一些诗是为舞台写的, “死亡天使”、“十字架”等等,还有好几首诗,你影射舞台、哈姆雷特和木偶剧场。戏剧对你的作品有多大的影响? 赫鲁伯:我想,影响我的那些戏剧,和所有人一样,都是从莎士比亚到贝克特。只不过我有一种个人感觉,戏剧是另一种诗歌。我把戏剧和诗歌放在一边,而散文放在另外一边。我写不了那种连续不断的文本,中间没有沉默或静寂,没有分节或分幕,没有副题或字幕。这在戏剧和诗歌里是有的。写每章二十页的小说,我觉得很不自然而且很强迫性,我不会这么做。除了意识的流动;如果一个人有天赋,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在自由流动的、至关重要的和意义深远的河流上……。我喜欢散文像一条河流,而不是像一条人工水道。所以,当我有时间写点不同的东西,我会写某种戏剧,有很多次我觉得自己有了一部戏剧的构思,但尚未成型。当我开始写诗,我已经想好了第一行,而戏剧,我只能想到第一幕。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听过不同的作家谈论过这个过程,某一些,尤其是小说作者,我听他们说过,他们在写小说前就清楚知道小说该如何收尾。你觉得只知道第一行或第一幕是优点吗,写作更加成为了发现的过程? 赫鲁伯:我需要知道戏剧该如何收尾。因为预定结构是必要的。这样我们才不会胡乱收尾。 正好与诗歌对立? 赫鲁伯:不。如果第一行诗去不到任何地方,我好歹知道我不得不终止这种风格。因此我开始把诗作为整体来构思,根据诗的整体结构,而它涉及到一种想法,我称之为与哲思相对立的诗思。我有了诗思才会开始写诗,否则我会迷失,如果今天你给我一个房间、一张纸、一支笔,然后要求我写一首诗,我会在这里花上两天,更像挨饿而不是写诗。若之前我不知道诗的大致意图,我不会去写。 你曾说,科学既是理论的,也是实验的,而艺术只是实验的。为什么你认为艺术艺术缺乏理论的成份? 赫鲁伯:艺术是一门分工劳动。有理论家,也有实践艺术家,而按照定义,太多的实践艺术家不阅读任何理论,而且他们憎恨理论家,尤其是他们的作品的评论者。我不明白我自己是怎么被训练成科学家的。我接受任何评论,作为一条真正讯息,而不是作为对我的人身攻击。我可不是装的,我真的这么觉得。而且我被训练成更多地责怪自己,而不是责怪别人。因此我看待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要比大部分作家积极一些,他们总是宣称“他们根本不懂我们,他们不动脑筋,他们基本上在操纵文学。”。我们有一个有趣的情况。在我们的文学或文化刊物上,我们的理论要比真正的文学多得多。一份最主要的文学刊物上,诗和小说只占30%,其他全是没人读也没人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或者文学理论。它还是周刊,真是阅读的负担啊,除了这份杂志,你不用读别的了。 赫鲁伯:不,只是在争夺地盘,而且我理解编辑的用心,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马列主义年代,能被接受的,只有所谓马列主义者或者乔装成领导以为的马列主义者。如果贴上了存在主义或后现代的标签,很可能是致命的罪过。因此,现在他们拼命朝这个方向追赶。他们尽量介绍任何一种新思维的写作,只是想冲过更高信息的关卡。我必须说,这些刊物的智识水准比以前在共产主义时期高出了一倍。但它们的可接近性,它们的常规信息有点太微弱,太疏离了,而且实际上,他们也因此不如在共产主义时期那么重要,那么有影响力。你知道,在六十年代后期,不管什么,只要沾点哲学、人类学诸如此类的边,每个人都想读一读,甚至自己翻印,而今天这些“深刻思想”已经成了阅读的负担。它仅仅是人类心智的毒剂。 理论影响诗歌和小说吗?在这份刊物上,年青作家受理论影响吗? 赫鲁伯:完全不。我想年轻作家受他们自己影响。基本上还好,但可惜人的自我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内在自我看起来就像其他的内在自我。我写过两首诗,是说在我们内里的深处,有荷尔蒙的以及其他调节性的影响,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内里都有同样的深度空间,或者同样的“幽暗花园”,如威廉斯?卡洛斯?威廉斯所言,“内在自我的幽暗花园”。然而,什么令我们如此不同呢,是外部经验。当你想被人理解,当你想拥有一点影响力,你必须瞄准它。 二 [提问者:南非诗人Alan Finlay] 艺术和科学的共同根基是什么?
赫鲁伯:两者的共同根基是高雅地称之为“创新”的东西,而我称之为获取恰切思想的技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具体到这条艺术准则或那条科学准则的恰切问题。否则的话,两者间极少共性。可能两者都需要运用人的能力、才干吧;例如想象力,例如分析思考的能力。 科学如何影响你的写作?
赫鲁伯:仅限于我和真实的关系。这恐怕会被说成是“怀柔”手段吧。我认为每一件事实,每一种标准,都需要审核、分析和批评。这是我从科学里学到的。现实,人,自然界的真相太复杂了, 因为我认为在诗歌里有清晰的表达是必要的。我不认为诗歌是辞藻和感觉的丛林。我需要明晰。谢默斯?希尼说我的诗是“完全裸露的诗歌”: 我的诗完全裸露,因此它们翻译起来相对容易。 你的诗《失肺综合症》以这样一个景象结束:只有外科医生写诗。
赫鲁伯:这首诗是写一种罕见的疾病,看上去像整个肺消失了。肺部只是一个大洞,而这是对人类灵魂的某种评述。我在另一首诗里说,一次成功的外科手术是第一诗歌——沿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分类法,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第一哲学是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莫扎特死于肾衰竭。如果他活在今天,肾衰竭是有办法解决的。他可以换肾,然后创作更多的交响乐章。 有哪一类问题,科学不能问,或不能答,而诗歌却可以?
赫鲁伯: 好,诗是一系列的问题。你在诗里看到的是基本隐喻。问题是,这个想法(不是哲思,而是诗思)可以制作成诗歌吗?第二个问题依赖于诗人的教育:多少人已经有了同样的想法?如果我们的记忆像电脑,我们就能发现某地某人已经写了几乎相同的诗歌。在科学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当下的趋势、当下的科学程式的一个结果。它们源于主流理论,而且必须遵循实验室里的既定技术的可能性。因此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基本上,如英国生物学家彼得?米达瓦所言,“科学是可解决的艺术”。或许,这样说来,诗歌是可想象的艺术。 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反对神秘主义?它只是处于初始阶段的人类智慧,也许可以这样说。
赫鲁伯: 的确。我不喜欢迷信,包括历史悠久的迷信。现实在变化,在这星球,在这宇宙,每样东西都在变化, 为什么人类的态度不变化?但你明白,我只是在说我自己。这并不是万灵的药方。如果每个人都持同样的观点,世界也就成废墟了。我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对我而言,韦拉德米尔·霍朗(Vladimir Holan)是最伟大的捷克诗人之一,他是性格内向的那类人,词语的神秘主义者,一颗深深孤绝而分裂的人类灵魂,他只相信自己的才华。对于我,真理有赖信息,有赖有效的信息,这是必需的。对于其他人,真理可能是孤立个体作为媒介,传递直觉、洞察力等等东西的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我可能会说这样会铸成大错。但讲到诗歌,它却可能是一种有趣的诗歌声音。
因此对于你,创新是发现一条新路,因为我们经常身处新形势下?
赫鲁伯: 我不喜欢这类崇高的词汇,例如“创新”,但是确实,创新是某种近似于深刻又激进的变革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像人的天性、人的本性,是不变的?我怀疑。我想,人的本性是变化的,就像世界上任何生物的本性或任何现象的本质一样,一直在缓慢地变化。当然,这是肉眼看不见的。人的本性一百年不变。中世纪的人或古代人或猎人和庄稼汉,我们对他们的深层心理还是知之甚少。 在你的企鹅版《诗选》的前言中,艾尔瓦雷兹(Alvarez)写道,你更关心诗里说出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去说。然而很多诗人会说,对于他们,诗歌的音乐才是重要,也就是如何去说。对很多诗人而言,歌才是诗的本质。
赫鲁伯: 诗可能是吟唱,可能近乎歌。吟唱是俄罗斯诗歌或拉美诗歌的方式。典型的捷克抒情诗体是歌唱的抒情诗体。塞弗尔特,捷克的诺贝尔奖得主,把他的许多诗叫做歌。我学过六音步诗,我最早受到的文学教育是希腊的,古典希腊文学。严格的音步会令意象和思想的形成受到限制。我拒绝那些“预设性”的限制,我要无拘无束地找到对比情境,以构筑诗的主要隐喻。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诗并不是剁成短行的散文。哪怕是自由诗也得有章法,而且不能是惹人心烦的章法,要不然你会在不知所云或难以理解的散文里迷路。 捷克社会在过去五十年发生了这么多剧变,你怎么看待你在这种语境里的诗歌?
赫鲁伯: 当一个人生活在压迫之下——多多少少来自社会和政治形势,他通常倾向于写一些更朝气蓬勃的,甚至是好玩的,更乐观的诗歌。当你孤身一人,当你自由自在,你会放松自己。你甚至可能会脾气暴躁,郁郁寡欢,悲观厌世。我有一种感觉,诗人在幸福快乐的情况下会失去他们的一部分本性。他们不确定要说什么。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抱怨了。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制度是混沌无序的制度,我注意到它在各个层面都解体了。压迫是一件事,普及化的和合法化的混乱,道德混乱,行政混乱又是另一件事。在这种整体混乱不堪的状况下,诗歌是秩序的最后资源。在一个完全有序而开放的民主社会,诗歌只不过扮演反对的角色,创造某种骚动,某种个体的混乱,这些可能挺有趣的。 你从历经多年的东欧社会主义里走出来,怎么看90年代的全球资本主义浪潮?
赫鲁伯: 这当然不好说。谁喜欢资本主义?即便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所谓社会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人。更何况现在资本主义成了有点肮脏的名词。我们出生在有平民左翼理想的中欧。生活的商业化,文化的商业化,对我们是威胁。不过,如果另一选择是贫困、饥谨和种族战争,那么资本主义始终要好一些。一个富裕、科技进步的社会却没有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在新的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我们的诗歌觉得受到忽视。不管怎么说,诗歌的主流从不试图接近民众。我们越觉得被孤立,我们就越会被玄奥而繁琐的自闭者以及后超现实主义的赝品孤立。 在南非我们也有类似的情况,大部分诗歌无人读,无人听……
赫鲁伯: 诗歌什么时候真被大多数人阅读过?只不过在某些文化,诗歌被当成骑士或武士的属性。否则,诗歌只有极有限的人群才会注意。 你在别处的谈话里,你对两种诗做了区分,艺术诗歌和出乎必然的自发诗歌,后者的写作者可能没想过他们是诗人。
赫鲁伯:我想关键是:它是谈某种玄奥问题呢,还是谈每人每天在生活里都要面对的那些问题?昨天我看了“真相及调解委员会”开会的情形,我被那些贫苦、饱经磨难的黑人受害者的讲述深深打动了。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残酷的诗歌,艺术的诗歌无法和它相提并论。而最近我刚好读了二战期间的诗歌。当时最有力量的诗都是普通人写的,开战机的上尉,华沙犹太区的遇难者,等等。这表明诗歌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我曾写过,“诗无处不在,这是最伟大的反诗论”。我是说,反对作为文学的诗歌;我是说,反对仿造的诗歌。因为我认为,诗歌是嵌在每个人的生活里的,它在激烈的体验里浮现,它在人类历史里较戏剧化的时期浮现。 1996年7月
来自群组: 读睡诗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