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阅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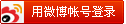
x
齐奥朗:信仰的诱惑

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EmileMichel Cioran,1911-1997),有罗马尼亚语及法语创作格言、断章体哲学著述传世,以文辞精雅新奇、思想深邃激烈见称。生于罗马尼亚乡村一个东正教神父家庭,曾在大学攻读哲学,1937年获奖学金到巴黎留学;将近60年,一直在巴黎隐居,先住旅馆,后住在阁楼里,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接受采访。他曾郑重告诫自己:“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局限于一场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显然,他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孤独。
在喧嚣的、充满功利和诱惑的20世纪,齐奥朗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奇迹。在孤独中思想,在孤独中写作,在孤独中同上帝争论,在孤独中打量人生和宇宙——孤独成了他的标志,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在孤独中,齐奥朗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时间之外”,身处“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这种绝对的孤独必然会留下它的痕迹。《生存的诱惑》《历史与乌托邦》等著作奠定了他哲学家和文学家的重要地位。移居法国后,他一直用地道的法语写作,文笔清晰、简洁、优雅,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黑色幽默。在他看来,“写作便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因为“作家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生物,通过言语治疗自己”。他甚至感叹:“假如没有写作本领,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他的文字常葆有剖析和挖掘的力量,准确、无情,直抵本质。
(《眼泪与圣徒》英译序)
文 | 伊琳卡·扎里佛泼尔—约翰斯顿 译 | 沙湄
“作者已死”是一个我始终没能适应的概念。一次又一次,当我打开一本爱不释手的书,“已死的”作者就会再度归来,缠住我不放:就好像阅读是一道将他召回的符咒,他徘徊的魂魄常在我心灵之眼前。阅读过程中,我全心都为捕捉这幽灵、了解他、“成为他”的热望所据。若没有“死去的”作者复活如初的想象,我就无法阅读。
E.M. 齐奥朗是一位尤其需要去想象的作者。身为作家,他特别精熟于在文本中玩弄作者虚构的生灭游戏,实际情况使这一游戏愈发复杂:他在现实中拥有两种生涯、两种身份、两种作者语态——1930年代的罗马尼亚齐奥朗,1970~1980年代的法国齐奥朗(有名得多)。我对齐奥朗的想象,始于翻译他的第一部罗马尼亚语著作《在绝望之巅》(原书于1934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英译本于1991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目前我完成了他另一部罗马尼亚语著作的翻译,即1937年出版于布加勒斯特的《眼泪与圣徒》(出版前夕,齐奥朗离开罗马尼亚远赴巴黎,再也没有回国)。此际,我发觉自己又陷进了一团乱麻的想象,撩人的问题挥之不去:这人是谁?
在共产主义罗马尼亚被当作不存在的人从历史中抹掉,在精英知识分子圈外的西方罕有人知,最后,齐奥朗又在临终的可悲病症中避开了我的追问。这位风格大师此时只能用眼睛来说话了。这其中有一种残酷的诗性正义,因为他在《眼泪与圣徒》中沉思的神秘主义经验极为强调眼睛、强调对不可见事物的观看,以及寻求近切地认识一种超常的非经验实在。既然神秘主义的语言观念是悖论性质的——只有沉默才能涵盖无限和不可见者——那么,他此时保持沉默或以目传言也许正是得体之举。齐奥朗现在已是全然的局外人,正如他的众圣徒。其实在许多方面,他一直都是个局外人,但如今他向“幽微之境”的迁徙不留余地而且不可逆转。他炽热的绿眼睛宛如两潭不属于此世的光源。去年夏天我看着这双眼睛,说起我对他的众圣徒所下的侦探功夫,其中有些人是多么难于追查——实际上,有些人我始终未能得手。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选这么个晦涩的主题来写。近来,圣徒和天使又变得颇为时髦了,但我禁不住怀疑,1930年代是否还有别人像他一样熟知这些圣洁人物。齐奥朗仿佛从远处聆听我,眼里燃起淘气的光彩,嘴唇紧闭。他已经从这个纷扰的世界中抽身,将文字的华美之袍留在我们手中,供我们大伤脑筋。我的作者并未死去,他不过是遁入了另一个世界,活在彼处,引诱、撩拨、挑战他的读者,刺激她奋起直追。从此我将跟随他,踏上读者寻找作者之途。初次发现他会是在哪里?
罗马尼亚,1930年代中叶。意气昂扬的青年,已然是新生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明星作家,齐奥朗长时间泡在一座特兰西瓦尼亚图书馆里(位于故乡锡比乌)孜孜研读圣徒传记。这位当代的圣徒传作者,“梦想”自己是“这些坠落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圣徒的〕年代记编者,他们内心激情的知己,为上帝而失眠者的历史学家”。问题自然随之而来:一个健康正常、公开承认恋慕生命、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小伙子,为什么会想要“擅闯天堂”,一窥圣徒的秘密?在尼采《善恶的彼岸》的一个段落中,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迄今,最强有力的人在圣徒面前总是谦恭地低头致敬,视圣徒为克己和绝对自愿守贫的难解之谜——最强有力的人为何会如此俯首称臣?他们在圣徒身上发现了……高人一等的力量,它愿通过这种克制来验证自身;在意志的力量中,他们认出了自己的力量和权力之爱,并且懂得了如何荣耀它:他们荣耀圣徒时,便荣耀了自己身上的某种事物。此外,对圣徒的沉思使一种怀疑出现在他们心中:这么严重的自我否定和反自然行为不会是一无所求的……总之,这个世上的强力者学会了去拥有一种新的恐惧,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一个陌生的、尚未被征服的敌人:那就是迫使他们在圣徒面前停下脚步的“强力意志”。他们不得不去质疑圣徒。(56)
齐奥朗印证了尼采的洞见,他在《眼泪与圣徒》的首页即声明自己关注圣徒的原因,其形式是这本书承诺去探索的一个问题:“一个人是怎样弃绝自己并走上成圣之路的?”从圣徒弃绝此世的能力中,齐奥朗看出了他们的“强力意志”,他写到,圣洁是“帝国主义的”,它“吸引我的是温顺之下隐藏的自我膨胀之谵妄,它那以美善来掩饰的强力意志”。从法西斯主义到共产主义,各种极端主张撕裂了政治领域,身处其中的齐奥朗显然对强力意志十分着迷,尽管如此,他的敬畏中还是有一抹嘲讽的怀疑态度。他视圣徒为部分的自我、自我的另一面,这些虔信的存在主义者“活在火焰之中”,而“智者活在火焰之侧”。他在书中与圣徒发展出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有一次他写道:“我爱圣徒是因他们烂漫的天真。”他对圣徒的爱略带唯美主义的颓废意味:“我们不再信靠圣徒。我们只是钦羡他们的幻觉。”然而,激烈又刻毒的仇恨抵消了这份纨绔子弟式的爱。他多次承认,他恨圣徒是因他们将无可救药的受难癖遗留给我们,因为苦难“只能是徒劳而邪恶”。“人怎能不痛恨天使、圣徒和上帝?……天国令我恼怒,它在基督教的伪装下把我逼上绝路。”
《眼泪与圣徒》是对于圣洁的沉思,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圣洁。也就是说,并非传统圣徒传中因德性而受崇拜的殉道者和英雄,而是以灵性高度著称的神秘主义者,他们拥有关于上帝的私密知识,导致又一场“绝对在历史中爆发”。书名《眼泪与圣徒》与罗马天主教传统中“眼泪的恩赐”有关。《灵修辞典》(Dictionnaire de la spiritualité)将“眼泪的恩赐”描述为“一种复杂的现象,由特定的灵性情愫及其具体表征构成”。此书列举了神圣之泪的三种类型:悔罪的眼泪(恐惧懊悔的净化之泪),爱(或恩典)的眼泪,为基督受难而同情哀泣的眼泪。13世纪早期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开始,占主流地位的是最后那一类型的眼泪。
齐奥朗在文中反复提到因怜悯基督受难而流的眼泪,那是西欧神秘主义的特色。神秘主义“这一运动所朝向的对象超出了实际经验的限度”。它也是“对上帝之临在的直接而被动的体验”(《灵修辞典》)。这“运动”是一种逃避——通过祷告、默想和静观——逃离此时此地。其目标是与上帝归合,其核心是道成肉身与救赎的奥秘,因为基督的人性被视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凭着对受难基督的感同身受之情,人得以从“堕落”状态中获救脱身,与上帝归合,从而分有神性。眼泪被看作恩典的标记,上帝临在于人心的外部表征。对这恩赐的许多描述都强调眼泪不可言喻的甜蜜。而齐奥朗从一开始就把神秘主义话语拧了个倒转,因为对他来说,眼泪并不甜蜜,而是苦涩的:“当我探寻眼泪的起源,就想到圣徒。他们会是眼泪那苦涩之光的源头吗?”
齐奥朗书名中的圣徒属于一种新类型,大部分是平信徒,且多数为女性,人称“神秘主义者”(mystics)、“灵修士”(spirituels)、“冥想家”(contemplatifs)、“光照派”(alumbrados)。他们达致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是反神学、反建制的,仅仅基于直觉和情感。书中出现的很多名人都曾为西欧神秘主义文库留下经典之作: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Eckhart)、圣加大利纳·锡耶纳(st.Catherine of Siena)、圣女大德兰(st. Teresaof Avila)、圣十架约翰(St. John of the Cross);但不出名、不寻常的人物更多。在《眼泪与圣徒》中,齐奥朗把神秘主义者列在圣徒名下。因为对他来说,神秘主义者是与政治无关的、消极地默想着神的人,他更乐于称之为圣徒。他写到,圣徒乃是政客——尽管是“未遂的”政客,因为他们否定了表象:这些付诸行动的务实派男女,用乐善好施的行为表达了对人类的爱。的确,许多欧洲神秘主义者都是积极的改革家,欧洲政治游戏的严肃参与者(比如在把教宗从亚维农弄回罗马的事件中贡献过政治力量的圣加大利纳·锡耶纳)。所有圣徒——其中很多人属于托钵修会——都献身于慈善工作,在修道院墙外的世界里勤勉地服侍穷人病人。
欧洲神秘主义是暗含政治意味的宗教运动。它带有强烈的改革精神,这种精神成形于天主教教会官方体制的边缘,时时与之冲突;在这些圣洁的人看来,腐化堕落的教会已不再有能力悉心照料信众的灵性需求。这一运动在历史上贯穿好几个世纪,波及好几个西欧国家,从发轫之初(12世纪由圣伯尔纳铎发起)到13世纪末在德国、荷兰以及意大利的燎原之势,从16世纪在西班牙的巅峰状态到理性时代前夜在17世纪法国的最后余晖。尽管欧洲神秘主义跨越的国家为数众多,但正如米歇尔·德·塞尔托在《神秘主义的诳言》中所称,那是一种“临界”现象,肇始于现代性的开端,适逢统一的基督教欧洲行将瓦解之际,强大的世俗国家定型,新科学和新艺术的根基坐实。其结果是,“在一个分崩离析亟待修复的世界里,在一片衰落而‘腐败’的背景下,基督教激进主义的野心露出了端倪”(塞尔托原书,第14页)。面对基督教信仰崩溃、“基督教传统蒙羞”的情势,神秘主义者为重建真信仰奋而起行。例如,圣女大德兰和圣十架约翰都是其所属修会的改革家。他们就这样塑造了一种近乎异端的“基督教激进主义”,“在迷狂和叛乱之间摇摆”(塞尔托原书,第24页)。
齐奥朗明确强调了圣徒生涯中的政治因素,但在他看来,圣徒的慈善事工是其生平中最乏味的面向。令他着迷的是圣徒的眼泪、他们对痛苦的渴求,以及忍受痛苦的能力——亦即,受难的病理学,也就是齐奥朗所谓“受难的淫乐”,因为“苦难是世人仅有的传记”。从苦难背后,从圣徒通过苦修弃绝一切的可怕能力中,齐奥朗察觉出他们狂热的强力意志。
圣徒的著作往往以“对话”为标题,因为采取了与上帝对话的形式,“conversar con Dios”,正如圣女大德兰所称。塞尔托在对神秘主义话语的分析中指出,圣徒著作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首句宣称意愿,开篇的“我愿”(volo)既是狂喜的,表明避世的决心,亦是苦行的,表明丧失的决心(塞尔托原书,第229页)。塞尔托写到,这种发愿的行动“vouloir”也是强力的行动“pouvoir”。他援引了埃克哈特大师的一段神秘主义经典,大师写道:“凭这意志,我无所不能。”“我心所欲,必得。”(塞尔托原书,第170页)可是,圣徒想要占有并控制什么呢?齐奥朗说:“他们要征服的空间是天空,他们的武器是受难。” 圣徒的“强力意志”没有特定对象。他们想要拥有无限(“天空”)和上帝:即,他们想要一场不存在,因为正如波德莱尔所言:“上帝是惟一为了统治之利甚至无需存在的存在者。”于是,内在空间成了以意志为最高主宰的疆域,享受着不依赖于对象或环境的自律(塞尔托原书,第235~236页),内心或灵魂成了上演神秘主义戏剧的舞台,如圣女大德兰的《七宝楼台》(Las moradas)所示。
齐奥朗在《眼泪与圣徒》中全神贯注的正是这种既狂热又无谓的强力意志,想要去支配、去了解、去爱或者透过爱来了解的强力意志——它旨在一切,同时又旨在无物,即:上帝。然而,上帝对于圣徒来说是意义深远的虚空,对于齐奥朗来说却是缺乏意义的虚空,“上帝已死”,如同对于尼采。因此,本书批判了除徒劳而残忍的受难之外一无所获的强力意志。它既揭露又驳斥了圣洁的政治根基,最后将圣洁归入心理学或美学的范畴,因为圣徒终归是些顽固地否定表象世界的“未遂政客”。
尽管如此,谈论圣徒的“强力意志”,的确揭开了他们存在主义宗教经验的政治面向,并鲜明地将本书中的政治问题置于焦点。《眼泪与圣徒》创作与出版的历史语境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本书出版于1937年齐奥朗远赴巴黎之后不久,他于同年发表了自己最为激进和不加掩饰的政治著作《罗马尼亚的变形》(Romania’s Transfiguration)。这两本同时问世的书凑成了有趣的一对:一本是关于神秘主义的元批判著作,另一本是用神秘主义修辞来表达的政治小册子。《眼泪与圣徒》印到一半,出版商醒觉到内文惊世骇俗的性质而拒绝出版,最终由齐奥朗自掏腰包印行。齐奥朗告诉我,当年他是如何不得已离开原出版社,扛着一个装有长条校样的包,穿过布加勒斯特去寻觅别的出版商。
《眼泪与圣徒》一问世就引起了丑闻。它以简短警策的断章写成,形式和内容都让人立刻想到尼采。这是一部关于神秘主义的哲学著作,前后不连贯,而且是偶像破坏式的。颓废气息与书中反基督教的渎神腔调交相辉映,在罗马尼亚简直闻所未闻。但是,正如于斯曼在《逆天》中论及颓废的主人公德泽森特(Des Esseintes)时所说,要想亵渎天主教,你首先必须得是天主教徒才成。在齐奥朗文句的反基督教外表之下,汹涌着基督教的潜流。切切不要忘记,齐奥朗是一位基督正教(Orthodox)司祭的儿子,非常熟悉基督教信仰的教理。他在罗马尼亚的弟弟还记得那些消磨在酒桌边的漫漫长夜,齐奥朗常和父亲以及来自锡比乌神学院的神学家讨论复杂的神学问题。据他弟弟说,齐奥朗那段时间最着迷的是神学和音乐,这由他的文字得到了证实——文字始终是他内心执念的驱魔术——在其中,有关音乐的精妙警句与他对眼泪与圣徒的沉思纠结在一起。
作为一部关于灵性、苦修、为基督之爱而受难的著作,《眼泪与圣徒》显然属于1920和1930年代在罗马尼亚盛行的历史、哲学和政治著作中的一员。“灵性”正是两次大战之间罗马尼亚文化的热门话题,所以顶尖期刊《标准》(Criterion)在“辞典”专栏里用一篇长文来为它释义,这个专栏旨在界定时代的“首要理念”,确立它们的“流通价值”。文章特别指出,“‘新灵性’的问题”就是齐奥朗所属的“新生代”的问题。
正如尼采所言,被圣徒形象吸引的人绝非庸常之辈,无一例外是“最强者”。齐奥朗的“新生代”知识分子是由内心强大的人组成的精英团体,是被罗马尼亚复兴的使命感所驱策的一代。他们自视为“革命新灵性”的代表,根据《标准》文章的说法,这种灵性排斥同时代罗马尼亚文化中出现的其他灵性类型,同时又和它们有重叠:领袖魅力型哲学教授、新生代的导师纳埃·约内斯库那种传统的、基督正教的灵性,或其他年轻知识分子更为“人文”和人道主义的类型,比如彼得鲁·科马尔内斯库和康斯坦丁·诺伊卡。米尔恰·武尔克内斯库既是《标准》文章的作者,也是新生代的一员,他评价说,众多年轻作家“在米尔恰·伊利亚德带领下”欣然接受全新的“苦恼灵性”,其主要特征是“清醒,负面,一种悲剧性的怀疑想要由一种新人类的启示来证明自己无效,可惜这种人还没被生出来”。
这一代知识分子与天使长米迦勒军团(Legionof ArchangelMichael)、即后来的铁卫军(IronGuard)有政治关联,那是“一场具有强烈神秘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运动”,矢志于实行“道德和灵性的变革,通过回归基督正教的价值来达致民族‘复兴’,通过苦行和牺牲来获得‘拯救’”(沃洛维奇原书,第62页)。齐奥朗那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同情军团运动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惟一能触发“基督教革命”、导致基督教国家创生的政治手段。这些年轻的“当代”圣徒处于政治极度腐败和经济极度恶化的背景下,戚戚于强烈的终末感,卡在对失乐园的乡愁和对新耶路撒冷的不耐烦之间,被改革的欲望鼓舞着,但不幸,找到的政治寄托却是法西斯主义的铁卫军。
西欧的神秘主义和1930年代席卷罗马尼亚的神秘主义热,两者崛起的历史条件有很容易追寻的相似之处。撇开细节出入不论,这两个时期都以认同危机及政治与灵性的改革责任为特征。根据塞尔托的说法,“马基雅维里主义阶段”和“神秘主义者的入侵”在历史上有某种巧合的倾向(塞尔托原书,第153页)。结果是,“运用政治理性来创造共和或国家以替代模糊失效的神圣秩序的任务,建立圣所以聆听在腐败体制内寂然无声的成言之道(spoken Word)的任务,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平行的”(塞尔托原书,第154页)。实际上,完全可以像塞尔托那样论证说,欧洲的神秘主义并未在17世纪消亡,它只是退去了:“这个逆旅中的幽灵,在对知识满有把握的时代受到抑制,却从科学的确定性的裂隙中重新冒出头来,仿佛总是回归其诞生之地。”(塞尔托原书,第77~78页)此处的关键词是“有把握”和“确定性”。20世纪上半叶,欧洲饱受大动荡的挫伤。在备受折磨的欧洲政治与智识环境中,罗马尼亚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处的地位而极度缺乏对于自身的确定性,程度恐怕比其他欧洲国家更甚,结果变成了披着政治外衣的神秘主义重生的沃土。
《眼泪与圣徒》必须放在这样的智识与政治语境中读解,它既是对时代精神的表达,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神秘主义的狂乱里糅合着近乎渎神的反讽,令此书独树一帜,它在罗马尼亚引起公愤并惨遭谩骂的反应,也是独此一家。
细察齐奥朗1937年出版的另一本书——《罗马尼亚的变形》,有助于我们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充分理解《眼泪与圣徒》所发出的非同寻常的声音。《眼泪与圣徒》是对神秘主义话语的批判,《罗马尼亚的变形》却借鉴了神秘主义著作的修辞,将之挪用到政治领域。这本书是对于“变形的”或得救的罗马尼亚的政治乌托邦梦想,这个罗马尼亚有能力突破“子历史”的命运,从“二手国”变成“大文化”。在《眼泪与圣徒》里,齐奥朗将圣洁定义为“克服我们身为堕落受造物的状态”。在神秘主义观念中,圣徒占有上帝的意愿和救赎其实是同一回事。因此,救赎方案不必局限于灵性的范畴,可轻松地用政治术语来转化——神秘主义者与上帝在灵里的合一,变成了一个(小)国家之更宏大命运的实现:“我们全部的政治和灵性使命,必须专注于决心去意求一场变形,专注于改变我们整套生活方式的那种孤注一掷又激动人心的体验。”(《罗马尼亚的变形》,第47页)
在《罗马尼亚的变形》中,齐奥朗给出了他对罗马尼亚认同危机的解决之道:只有当罗马尼亚被一种与圣徒的狂热同等的力量驱策时,它才会克服身为“小文化”的、“堕落”的历史状态。此时,神秘主义者的“意愿”不是无对象的,它有了具体的政治内容,其舞台不是心或灵魂,而是历史本身:
罗马尼亚是一个没有先知的国度()……这个催人清醒的念头应当促使我们有所不同,在盲目的狂热中燃烧,被全新的异象照亮……关于另一个罗马尼亚的思想应当成为我们惟一的思想。固执于同样的历史次序等于慢性自杀……我们将不得不弃绝自己的清明神志(它向我们揭示了太多不可能性),在一个失明的国度里,去征服光……(《罗马尼亚的变形》,第49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依托于描述出神异象的神秘主义语言,实行灵性改革的意愿和实现文化伟业的意愿在此结合了。在青年齐奥朗看来,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的口吻就像个新的马基雅维里,印证了塞尔托对神秘主义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经常同时出现的洞察:
当一个民族在世界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时,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惟有在衰颓之中,当他们捍卫空无一物的内容,恐怖、罪行、兽性和背信弃义才显得卑劣而不道德;假如情形相反,这些品质有助于一个民族的上升,它们就是美德。一切胜利都是道德的……(《罗马尼亚的变形》,第41页)
齐奥朗的马基雅维里熟知尼采。上文援引的段落是对《善恶的彼岸》的附和,尼采在该书中对比了颓废和非颓废的历史时期,他写道:
某些强烈而危险的本能,比如进取心、大无畏、报复意识、精明、掠夺欲以及爱好权力,在那以前不但从总体效用的角度是必须推崇的——当然是在其他美名之下,并非我开列的这些——而且必须得到培养和陶冶(因为在面对共同敌人的共同危险中永远需要这些本能),现在却显得加倍危险——当它们缺乏宣泄途径——于是逐渐被斥为不道德并任人肆意污蔑。(《善恶的彼岸》,124)
我们就这样遇上了一种有趣的智识境况:同一位作者在同一年里出版了两本书,两本都弥漫着神秘主义气息,一本是狂暴的政治著作,另一本是对神秘主义话语之政治根源的批判分析著作。有人可能禁不住会说,《眼泪与圣徒》是关于神秘主义现象的哲学论述,透彻检视了这种现象的政治内涵,它那不幸的政治对应物《罗马尼亚的变形》则是对神秘主义原则相当粗俗务实的应用,与当时其他政治—宗教左右翼著作的步调十分一致。然而,齐奥朗在《眼泪与圣徒》中对待神秘主义的暧昧态度表明,即便在他写作《罗马尼亚的变形》的当时,此书在他心目中无非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即“自我膨胀的谵妄”。其中的神秘主义色彩极大加剧了该书的乌托邦谵妄特质,与齐奥朗高扬怀疑论与绝望的存在主义哲学自相冲突。齐奥朗和神秘主义者圣徒在《眼泪与圣徒》中爱恨交织的关系,使他在《罗马尼亚的变形》中为罗马尼亚问题提供的粗暴狂热的解决之道疑窦丛生。因此,《眼泪与圣徒》在某种意义上是齐奥朗自身的哲学挣扎,一份充满矛盾和歧义的文本;它与《罗马尼亚的变形》同时问世,源自同样的关切,暴露了另一份鲁莽幼稚的政治文本的缺陷,从而拆了它的台。
《眼泪与圣徒》的许多主题,是齐奥朗会在后期的成熟之作中一次又一次回归的主题:音乐,灵性,苦难,死亡,孤独,怀疑,绝望,颓废,上帝,以及虚无。作为一本关于神秘主义的著作,《眼泪与圣徒》既非神秘主义著作,亦非不带偏见、不带私人感情的哲学著作。总的说来,它比较像是尼采那种杂芜的哲学评论。散漫而轻松的口语化抒情风格,穿插着惊世骇俗的隐喻,私人的、推心置腹的、在戏谑与激昂之间交替的语气,掩饰了字里行间的精深学识,掩饰了它的书卷气,以及它评论神秘主义现象时的准确与严肃。《眼泪与圣徒》那种暧昧不明而且时常自相矛盾的特性,源自它在两种对立的内驱力之间根深蒂固的彷徨——对满怀激情并放弃一切去信仰的强烈渴望(《罗马尼亚的变形》也充满了这种热望),以及不信的激情,即绝望。
书中的核心人物是齐奥朗所谓“未遂的神秘主义者”,“不能彻底抛开一切现世羁绊的人”。因此他说“神秘主义的成功秘诀是挫败时间与分别心”,但他又说“在永恒里我禁不住听到一口丧钟的哀鸣:此即我不敢苟同于神秘主义之处”——几乎半个世纪之前就预见到德里达的《丧钟》(Glas)。“未遂的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骇人的怪诞角色:“绝对的激情在怀疑者的灵魂中,就好像天使被移植到麻风病人身上。”正如乌纳穆诺的殉道者曼努埃尔·布埃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卡拉马佐夫,或热内的罪犯圣徒,他们同属于存在主义弃儿的家族,永远游荡在历史与永恒之间绵延的无人地带。
齐奥朗那些未遂的神秘主义者得不到救赎。成功的神秘主义者把他们感到独自面对上帝的时刻当作出神的巅峰状态来赞颂,即圣十架约翰所谓“soledaden Dios”。齐奥朗却抱怨说他无法感到“在上帝之中得其所哉”,说他终身都会“在祂之中背井离乡”。对于“成功的”神秘主义者,上帝正是欲望的对象,是强力意志的目标,可是对于齐奥朗,无论他多么拼命地力求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去爱、去信,他的热情总是会被怀疑和绝望釜底抽薪。他纠结于尼采的断语“上帝已死”(齐奥朗说得更诙谐:上帝是“遍及宇宙的缺席者”)。他揭穿了众圣徒不可饶恕的幼稚:他们“从来不曾自问‘上帝之后怎样’,为此我无法原谅他们”。未遂的神秘主义者的绝望——“我主啊,没有你,我是蠢的,而有了你,我会是疯的!”——以及他那存在主义的怀疑——“怀疑将我带到祂那颗心的阴影处就止步不前了”——混合了一点儿虚张声势,一种罗曼蒂克的、撒旦式的姿态。齐奥朗说,我们的用途是取悦一位孤单的上帝,我们是“绝对者的可怜小丑”。但他以“在痛苦的狂乱中抵制上帝”的无畏行动,拒绝在上帝的娱乐节目里出演角色:“我,带上我的孤独,与上帝对峙。”
齐奥朗关于神秘主义的论述以未遂的神秘主义者的形象为核心,是对神秘主义话语的一种刻意为之的、亵渎的滑稽模仿。不信的神秘主义者的声音引入了一个新视角,即绝望的视角,从而为神秘主义经验提供了一副新腔调,蓄意而悖谬地歪曲其原意。例如,“天堂从绝望的视点看去”就成了“幸福的坟墓”。在神秘主义经验中,默想和祈祷是通向上帝的重要步骤,但它们对于齐奥朗来说正好相反:“必须对上帝朝思暮想,以便将祂耗尽,把祂变作一堆陈词滥调。”对于神秘主义者,活在上帝之中的是惟一真确的活法;对于齐奥朗,那是“存在之死”。
不过,他最频繁的抨击目标是神秘主义的一个关键面向:受难,把效法人—神基督那种争胜的受难当作获得神性的惟一手段。神秘主义者的苦难有其预期的救赎内容,即达到在上帝之中的完美。而齐奥朗却放开伦理观点,从审美的角度去看待苦难,因为令他着迷的是“受难的淫乐”,而非受难的德性。他视苦难为人类悲剧性境况中的基本要素——“苦难是世人仅有的传记”——而且漫无目的,因为在基督教关于苦难的固有观念中,苦难并不提供救赎的承诺,即便神秘主义无所不用其极。苦难,尽管齐奥朗从它背后看出了强力意志,却是毫无效用的,除了制造更多残酷而无意义的苦难之外一事无成。“自从意识被创造出来,上帝就出现在祂的真光中,成为又一份虚无。”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救赎的余地。未遂的神秘主义者的绝望,他的最高盼望的失落,以及通过乌纳穆诺所谓“生命的悲剧感”对此的克服,都采取了尼采对基督教的抨击形式。在抨击中,齐奥朗的语气一会儿刻毒一会儿挖苦:“我不知还有什么罪比耶稣的更严重了”;“终极残酷就是耶稣那种:在十字架上留下一笔血迹斑斑的遗产”;耶稣,“这嗜血又残忍的”基督,“幸亏死得早。要是他活到六十岁,给我们的肯定不是十字架,而是他的回忆录”。在一个段落中,齐奥朗回顾了基督教历史中的暴行导致的劫难,也预见到很快就要出现在自己祖国的暴行,他被宗教的暴力和苦难所慑,(早于乔治·巴塔耶的《欲神之泪》或勒内·吉拉尔的《暴力与神圣》好几十年)写道:“基督教乐见血迹斑斑的景象,它的殉道者已经把人世变成一场血浴。在这个血色黄昏的宗教里,崇高败给了邪恶。”
假如对齐奥朗而言,神秘主义原则在灵性领域里终归是失败的,那么它的政治对应物也注定会失败。这个有如许怀疑和阴影的人,除了在无能为力的狂怒所引起的痉挛中胡言乱语,或者在他写作《罗马尼亚的变形》时那种“自我膨胀的谵妄”中咆哮,还能做什么呢?他会不会像乌纳穆诺笔下未遂的圣徒曼努埃尔·布埃诺那样,是在宣扬自己也无法相信的东西?如果说《罗马尼亚的变形》有意为罗马尼亚的生存与政治困境提供解决方案,同时问世的对应物《眼泪与圣徒》则揭开了硬币的另一面,即:只要有诚实而绝望的怀疑,就没有解决之道可言。结果,就在齐奥朗写下自己最骇人听闻的政治小册子之际,我们借由《眼泪与圣徒》,得到了一幅呈展他复杂而分裂的心灵的透视图:
那些被上帝缠住的灵魂就像一泓朽败的泉水,半残的花朵与腐烂的蓓蕾杂陈其间,恶臭阵阵拂过。那是……勒索钱财的圣徒之灵,是尼采那种敌基督的基督徒之灵。我深恨自己不是出卖上帝并尝尽痛悔的犹大。
在1930年代的罗马尼亚,两件绝对事物缠住了齐奥朗年轻的灵魂,两者他都无法相信。这种情形之下,他的下一步举措看来不可避免:要么自杀,不然就自我放逐。1937年,《眼泪与圣徒》出版之前几个月,他离开布加勒斯特,一去不返。再次听到他的消息,已是在1949年的巴黎,他的第一本法语著作《解体概要》出版的那年,他已然抛弃了罗马尼亚的语言和身份,屈服于一个夙愿已久的执念:成为一个来自乌有之乡的人。
来自群组: 读睡诗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