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阅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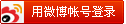
x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之一。他曾当过新英格兰的鞋匠、教师和农场主。他的诗歌从农村生活中汲取题材,留下了《林间空地》、《未选择的路》、《雪夜林边小驻》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可福人岛么,祝福你吧小伙, 被神祝福的人我还没见过。 如果问谁说了“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很多读者会回答说是“济慈”,但是济慈没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那是希腊古瓮说的。这是他对一种艺术品的描述和评论,这种艺术品故意将现实生活的罪恶和困难、心灵的悲苦烦闷排除在外。比如,古瓮描绘了山区小城的城堡等美景,却没有描绘战争,而使城堡成为必要的正是战争。 艺术源于我们求美求真,并知道真和美并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每首诗都有爱丽儿与普洛斯彼罗角力的迹象;在好诗中他们好歹关系融洽,但也不无紧张。希腊古瓮说出了爱丽儿的立场;普洛斯彼罗的立场则由约翰逊博士说出,一样地简明扼要:写作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使读者活得更开心或活得更耐心。 我们希望诗要美,是言辞的人间天堂,永恒的乐土,令我们愉悦,正因其与我们艰难苦恨的有限人生恰成对照;同时我们又希望诗要真,向我们揭示生活的某种真相,使我们免于自溺自欺,而诗人若不写困难、痛苦、混乱、丑陋,便不能带给我们真相。虽然每首诗都含有爱丽儿与普洛斯彼罗某种程度的合作,两者扮演的角色轻重在不同的诗中却各各不同:通常一首诗,有时候甚至是一个诗人的全部作品,我们都可以指出是爱丽儿为主还是普洛斯彼罗为主。 炎阳,凉火,被宜人的风所缓和, 凉阴,好嬷嬷,遮住我的白发吧: 让日照火烧和风吹,放松我吧; 凉阴,好嬷嬷,收裹我愉悦我吧: 阴影,好心的嬷嬷,别让我烧坏, 别让我快乐的因由变成悲哀, 别让我美丽的烈焰 点燃抑不住的欲望, 也别让炯炯的目光 瞄来瞄去把火看见。 (乔治•皮尔《拔士巴之歌》) 爬行到坡顶的路 仿佛是到了末端 腾空往天上飞去。 又仿佛拐了个弯 远远地穿进林子 在那里静止不动, 前提是树也静止。 任想象天马行空, 矿物油滴的爆燃 驱动我成吨车辆 却只能用在路上。 油滴关乎走多远 而几乎无关的是 遍天蓝和本地绿 所暗示于我们的 绝对的飞和休息。 两首诗都是用第一人称单数写成,但是皮尔-拔士巴的“我”与弗罗斯特的“我”却大不一样。前一个我好像是泛称,简直只是一种语法形式而已。你无法想象在宴会上碰见拔士巴。后一个我点出特定情形下的一个历史个体——他正开着汽车,身处某种地形之中。 拿掉拔士巴所说的话,她就会消失,因为她所说的话并不是对什么情景或事件的回应。如果我们问,她的歌唱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只有模糊的答案:一个美丽的少女,某个少女,在某个晴朗的早晨,半睡半醒地琢磨着自己的美丽,思绪中交织着自矜自赏和自怡悦的恐惧,说自怡悦是因为她并没有察觉到什么真正的危险;真正怕人偷窥的少女会唱出很不一样的歌。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我们喜欢这首歌或这类诗,我们不由得要说到语言,说到节奏的处理,元音和辅音的模式,停顿的位置安排,换语修辞的使用,等等。 弗罗斯特的这首诗就不一样,显然是对先于言辞存在的经验的回应,没有这种经验,就没有这首诗,因为这首诗的目的,就是要写出这种经验,并从中得出智慧。这首诗也不乏文辞之美——它是一首诗,不是传达信息的一段散文——不过相对于它所说出的道理,这是次要的。 如果有人突然要我举一个好诗的例子,我马上想到的很可能是皮尔的这种诗;但是如果我心情正激动,无论这种激动是悲是喜,并试图想起一首合适的诗来形容我的心境,那么我想到的很可能是弗罗斯特的这种诗。 爱丽儿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没有激情。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不足之处。人间天堂固然美丽,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会从中发生。 如果由爱丽儿来编选一部诗集,诗集中只选像维吉尔的《牧歌》、贡戈拉的《幽处》和坎皮恩、赫里克、马拉美这类诗人,情感狭隘单调,久而久之会让我们反感:因为爱丽儿的别名叫做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照水自怜、溺水而死的美少年——译注)。 有时候一首诗写的时候是普洛斯彼罗为主,在后人看来却成了爱丽儿式的诗。儿歌《我来给你唱个“一”》易诵易记,原本可能有微言大义。我们觉得它已经爱丽儿化的迹象,就在于我们对它提到的种种人物没有好奇心:我们是以人类学家而不是诗歌读者的身份,质问“百合一样白的少年”是什么人。 诗人自己也有可能因为他所写的诗而被人误会。比如,《莱西达斯》乍读好像是属于普洛斯彼罗,因为它宣称要写的是最严肃的事物——死亡、悲伤、罪过、重生。但我相信这是错觉。细看之下,我觉得只有外套是普洛斯彼罗的,被爱丽儿为了好玩穿在身上,因此问“加利利湖的领航人是谁”就跟问“没有脚趾头的Pobble是谁”一样无谓,在湖面上行走的只是阿卡迪亚的牧人,只不过他的名字也叫耶稣罢了。若是像读爱德华•李尔的诗一样读《莱西达斯》,我觉得它是最美的英语诗之一;若是照它宣称的那样,把它当普洛斯彼罗式的诗来读,那么我们就该像约翰逊博士一样,贬斥它麻木轻浮,不能给予我们所期待的智慧和启示。 爱丽儿为主的诗人有一大优势;他写不好只有一种情况——诗太浅薄琐屑。他对自己的一首诗最糟糕的评价莫过于写了等于没写。但是普洛斯彼罗为主的诗人写不好却有好多种情况。英语诗人中,绝少爱丽儿因素而竟成为诗人的,也许只有华兹华斯,所以诗若完全由普洛斯彼罗来写会是什么样子,他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例子。 鸟儿和鸟笼,这些都是他的: 这是我儿子的鸟儿:他养得 整洁而光鲜,有很多次旅行 这动听的鸟儿都跟他去了: 最后一次他把鸟忘在船上, 这也许是他有不祥的预感。 读这段诗,我们会说:“这人不会写诗。”这样的话却从来不适合用在爱丽儿身上;爱丽儿不会写的时候,他就不写。除了滑稽可笑,普洛斯彼罗还可能犯更严重的错误;由于他想要说出的是真相,一旦写不好,结果比浅薄琐屑还要糟糕。他如果写得不真,读者忍不住要说的话就不是“这首诗写了等于没写”,而是“这首诗压根就不该写”了。 弗罗斯特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普洛斯彼罗为主的诗人。他在《诗合集》的前言中写道: 声音是矿石碓里的金子。现在,我们要把声音单独提炼出来,扬弃那些剩下的渣滓。经过这样不断的提炼,我们最终会发现:原来,写诗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诗都呈现出它们各自独特的声音;而光有元音、辅音、句读、句式、词句、格律这些资源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借助语境-意义-主题……话又说回来了,诗歌不过是另一种表达的艺术,可以有声,也可以无声。但有声的或许比较好,因为更为深刻,经验的基础也更为宽广。(一首诗)始于愉悦,终于智慧……在对生命的一点澄清中结束——倒未必是什么大不了的觉悟,像教派赖以建立的那种,而只是对混沌一点暂时的遏制。(这一段借用Tommyleea兄的译文) 他的诗风我觉得就是C.S.刘易斯教授称之为“寡淡得好”的那种。诗始终用的是说话的声调,沉静而理智。除了卡瓦菲,我想不起还有别的现代诗人措辞比他朴素。他很少用比喻,全集中也没有一个词或文史典故会让不爱读书的15岁孩子觉得陌生。但是他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和经验。 尽管如此,她已在鸟的歌中。 而且她溶入鸟儿歌声的声息 已经在树林里存留了这么久, 所以它也许永远都不会消逝。 鸟儿的歌声决不该一成不变, 这就是她来帮助鸟儿的因缘。 如果这时他在看得见我的地方, 我希望他离远点,别看见我这模样。 谁都可能从声名显赫变得一文不名。 关键是当我年轻、充满活力的时候 我是否曾知道这就是我的结局。 看起来我好像不会有勇气当着 大家的面这般无礼如此放肆。 我可能有勇气,但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两段借用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前一段诗的情感温柔、快乐,心思却是受过教育的人才有的那种。后一段诗的情感激烈、悲哀,说话人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不过两段诗的用词同样朴素。有几个那男的所用的词,那女的自己不会用,但没有一个是她不懂的;她的句法比那男的稍微粗糙一点,稍微而已。但是两人的声音听起来都很真实,却又截然不同。 弗罗斯特的诗歌语言是心智成熟的人的语言,清醒,节制,不说梦话或激情万丈的话。感叹句、祈使句和反问句很少见,除非是在引用的话中。这当然不是说他的诗缺乏感情;我们常常意识到所说的话背后有强烈乃至激烈的情感,不过语言很克制,仿佛他的诗有一种听觉上的贞洁。弗罗斯特即使想写,也写不出因为绝望而不加掩饰的痛吼,不像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但是写出下面这些诗句的人一定对绝望很熟悉: 我曾立定不动,止住脚步 当一声,被打断了的呼喊 从邻街传来,越过了房屋 但不是叫我回去或说再见 而在远处,高得不似凡尘 有只透亮的时钟高耸倚天 宣告着不错也不对的时辰 我已经是个熟悉黑夜的人。(这一段借用江枫先生的译文) 每种风格都有它的局限。弗罗斯特的诗风写不了瓦雷里的《蛇之草图》,瓦雷里的诗风也写不了弗罗斯特的《雇工之死》。像弗罗斯特这种接近日常语言的诗风必定是当代的、活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诗人才有的风格,不适合用来写古远的题材,因为古今差异显著;也不适合用来写神话题材,因为神话题材超越古今。 弗罗斯特写约伯的《理性假面剧》和写约拿的《仁慈假面剧》在我看来都不成功,都有点故意披上了现代的服装。 这样的诗风也不适合诗人需要代表CivitasTerrenae(人的城市)公开发言的正式场合。弗罗斯特甚至在戏剧作品中也是一个人自说自话的调调,说着心中所想,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谁在听。这种方法当然跟所有方法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比大多数方法更有深度。如果用来写有关个人情感的诗,这是良策。不过,如果用来写大家关心的有关公共事务或观念的主题,那可能就是失策了。弗罗斯特为193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国家党代表大会写了《培育土壤,一首政治田园诗》,当时就被自由主义左派批为反动作品。我们今天再读,奇怪他们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但是诗中那种大人物炉边闲话式的“我是普通人”姿态还是让人来气。我们宁可哥伦比亚大学请的是叶芝;他可能会说些荒谬绝伦的话,但能够演一台好戏。我们作为市民而不是私下的个人,在诗人谈论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事情的时候,所指望于他的,正是一台好戏。可能弗罗斯特自己也觉得不自在,这才在这首诗的最后也是最好的两行写道: 我们太过于分不开。而各自 回家意味着神志清醒过来。 任何以澄清人生为目标的诗歌必须涉及两个问题。所有人,无论读不读诗,都努力要澄清这两个问题。 (1)我是谁?人和其他生灵的区别是什么?两者之间可以有哪些关系?人在宇宙中处于什么位置?有哪些生存状况是人必须接受的宿命,想要改变也是徒然? (2)我该成为谁?那些人人钦佩该当作楷模的英雄、可靠的人有哪些特点?反过来,人人都该引以为戒的粗鄙的人、不可靠的人又有哪些特点? 这些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想找到答案,在任何情况下都普遍适用,不过我们据以考量的总是此时此地的经验。比如,任何一个诗人对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有什么话要说,一部分取决于他所生活的地方的地形和气候,一部分取决于他个人的性情气质对这种环境的反应。热带长大的诗人同哈福德郡长大的诗人观念不一样,快活合群的胖诗人同忧郁内向的瘦诗人看法也不一样。 弗罗斯特诗歌的气质是新英格兰的气质。花岗岩的新英格兰地区山多林密,土壤贫瘠。冬天严寒持续很长时间,夏天比美国大多数地区温和舒适,春天很短,来去匆匆,秋天慢悠悠,美丽多变。由于临近东海岸,是最早有移民定居的地区,但随着大西部的开拓,人口开始减少。夏天会有游客和买得起消夏别墅的城里人去那里,不过很多曾经开发过的土地已经抛荒了。 废弃的房子是弗罗斯特喜欢的意象之一。在英国或欧洲,废墟让人想起的要么就是历史变故,战争或圈地等政治运动,要么就是像废弃的采矿区建筑这种,让人想起的是辉煌不再,不是因为自然太强大,而是被掠夺光了。因此,欧洲的废墟唤起的往往是人类的不义和贪婪,还有自大受到报应这一类思绪。但在弗罗斯特的诗中,废墟是反映人类英雄气概的意象,是胜算无多的负隅顽抗。 一个风疾云乱的傍晚,我奉命 来到一座木板搭建、黑纸糊强、 只有一门一窗一个房间的房子, 这是方圆一百英里被伐光了树木 的山区荒野中惟一的栖身之所, 可如今屋里既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 (不过这屋里从没有女人住过……) 从这儿再往前到高高的山坡上, 在那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方, 我父亲曾盖起小屋,围住清泉, 并筑围墙把小屋清泉圈在里边, 使我们一大家人能够维持温饱。 我们家一共有十二个姐妹兄弟。 大山似乎很喜欢这派勃勃生机, 而且不久之后她就认识了我们—— 今天她也许叫不出我们的名字。 (毕竟姑娘们都已嫁人改了姓氏。) 这山曾经把我们推离她的怀抱。 如今她怀中树木葱茏枝繁叶茂。(这两段借用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我翻阅弗罗斯特的《诗合集》,找到了21首季节是冬天的诗,而春天的诗5首之中有两首地上还有残雪;我找到了27首时间是晚上的诗,还有17首暴风雨天气的诗。 他的诗中最常见的人类处境是有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妻,在大雪封林的夜晚,孤零零地待在一所与世隔绝的小房子里。 在对面那座高高的山上, 在我以为没有道路的地方, 一盏车灯闪出眩目的光彩, 开始蹦下一道花岗石台阶, 像是一颗星星刚落到地上。 在与那山相望的我家树林中, 我被那并不熟悉的光所触动, 它使我感到不再那么孤独, 因若是今宵黑夜令我烦忧, 旅行者也没法消除我的忧愁。 我们看啊看啊,可我们究竟在哪儿? 我们比以前更清楚我们在哪儿吗? 今夜它又是怎样架在夜空和那位 有一个熏黑了的灯罩的人之间? 它的架设方式和以前有什么不同?(这两段借用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在《两个看两个》中,以一头公鹿和一头母鹿为代表的自然以同情回应以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为代表的人类,不过这首诗的观点认为这种同情的回应是奇迹般的例外。《它的大部分》中描述的那种回应才是正常的。 有天早晨从那遍地碎石的湖滩 他竟对生命大喊,它所需要的 不是它自己的爱被复制并送回, 而是对等的爱,非模仿的回应。 但他的呼喊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除非他的声音具体化:那声音 撞在湖对岸那道峭壁的斜坡上, 紧接着在远方有哗哗的溅水声, 但在够它游过湖来的时间之后, 当它游近之时,它并非一个人, 并非除了他之外的另外一个人, 而是一头巨鹿威风凛凛地出现……(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不过,弗罗斯特却不像梅尔维尔那样,认为大自然对人怀有恶意。 它对人类的善肯定稍多于恶, 即便说只多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 不然我们的生命不会持续地繁衍。(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大自然倒可以说是“人类严厉的保姆(DuraVirumNutrix)”,她表面上的冷漠和敌意激起了人类的力量和勇气,使人类顶天立地。 勇气不能误认作浪漫的大胆。勇气包含谨慎和精明, 所有愿意活下去的我们 都拥有一个小小的哨子, 一有风声我们便会吹哨, 然后全都钻进农场地里。(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甚至还包含理财有方, 最好买些友谊守候在身旁, 这样便可以死得体面风光, 有总比没好。早防,早防!(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欧洲也有诗人对人类的孤独处境和大自然对人类价值的漠视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跟一个美国诗人比起来,在表达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生活在人烟稠密甚至过密的乡间,大地经过多个世纪的开垦,已经带有人类色彩,他们写起来,只好用抽象的哲理或不常见的非典型意象,以致他们说的话就像是理论和性情强加给他们的,而不是基于事实。弗罗斯特这样的美国诗人就不一样,他可以借助事实,而事实,是任何理论都必须说清楚的,也是任何性情都必须接受的。 弗罗斯特的人类不但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也是孤立的。在弗罗斯特的诗中,即使有也很少响起怀旧的调子。他写起童年的诗来,比如像《野葡萄》这首诗,不是把童年看作神奇的伊甸园,哀叹它消逝得太早,而是看作一所学校,在那里接受了成人生活的最初教育。他最好的长诗中有一首《世世代代》,背景是新罕布什尔州鲍镇斯塔克家族的祖屋。鲍镇是一个岩石遍布的小镇,农业已经没落,斧斤消失之后,林莽横生。斯塔克家的大宅已经只剩下地窖坑,还是在偏僻的小路边。诗中描述的事件是斯塔克家族后代的聚会,这是州政府的宣传噱头。人物是一个少男斯塔克和一个少女斯塔克,他们是远亲,祖上自然是一家,但是他们对祖宗毫无了解。男孩为向那女孩献殷勤,开始编故事,还学祖宗的腔调说话,暗示结婚,在旧屋基上建一座新别墅。这就是说,真正的过去他们既不了解,又觉得虚幻,在这首诗里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为生者提供相逢机会罢了。 跟格雷一样,弗罗斯特也在荒废的墓园写过一首诗。格雷关注的是不知名姓的死者的生平,过去在他的想象中比现在更让人激动。而弗罗斯特不作什么回忆;触动他的是伴随着人的恐怖死亡已经离开,像拓荒者一样动身前行了。 这样回答也许不乏机敏—— 告诉墓碑人们憎恶死亡, 从今以后永远不再死去。 我想墓碑会相信这弥天大谎。(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他觉得人的短暂一生珍贵之处在于时时刻刻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开始。 有谎言总是说没有一样东西 会在我们的面前出现第二次。 要是这样,我们会是什么下场? 我们的生命本身就依赖事物 的重现,等我们内心做出回应。 咒语重复一千遍也许就有灵。 弗罗斯特写了不少田园诗,无疑也很喜欢用那些传统认为典雅古朴的体式来描写民主社会的现实。若说新英格兰的地形没有阿卡迪亚风味,它的社会生活也一样没有;那种无所事事、一心只想培养欧洲田园式情致的有闲阶级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当然,同所有社会一样,这里也存在阶级差别。在新英格兰,英格兰-苏格兰后裔的新教徒认为他们比天主教徒和拉丁族裔的新教徒出身高贵,而最体面的新教教派是公理会派和上帝一位论派。比如,在《斧柄》中,那新英格兰农民就自觉进邻居巴普蒂斯特这个法裔加拿大人的家里是纡尊降贵。 只要他不过分溢于言表,我就不会 介意他因我上他家而欣喜若狂, (如果他欣喜若狂的话),他知道 我这下必须作出判断:他那些 不为旁人所知的关于斧子的见识 在一个邻居眼里是否毫无价值。 这法国佬虽一心要融入新英格兰人, 但要是他不能赢得点声誉将会很难!(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而在《雪》中,科尔太太这样看待福音会牧师梅泽夫: 一想他有十个孩子就 令我厌恶,而且最大的也不到十岁。 我也讨厌他那个小得可怜的教派, 就我所听到的,那个教派不怎么样。 不过在这两首诗中,都是邻里压倒了势利。那新英格兰农民承认巴普蒂斯特技术高超,科尔一家人担心了一夜,听说梅泽夫冒着风雪安全回到了家才安下心来。 在弗罗斯特的田园世界中,传统那种老于世故、疲于生活的朝廷官员被书卷气的城市居民取代,常见的是夏天在农场打工的大学生;他遇到的乡下人既不是可笑的乡巴佬,也不是高尚的野蛮人。 在《一百条衬衫领》中,一位文气害羞的大学教授,在一家小镇旅馆的卧室里遇见一个喝威士忌的胖大老粗,后者代表当地一份报纸在周围农场收款。如果说读者最后同情的是那大老粗,不是大老粗被写出了美感,也不是那教授令人讨厌。教授心存好意——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如果不是出于真心,起码是出于原则——但是一种使同情心和兴趣变得狭隘的生活方式使他也受到了毒害。大老粗的形象能逆转靠的是他无拘无束的友善,这友善完全发自内心,不是专业推销员的客套。他虽然粗俗,却不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一般人会认为他们并不像你 喜欢见到他们那样喜欢见到你。” “噢, 因为我要他们的钱?我并不想要 他们拿不出的东西。我从不催债。 我来了,他们想付就顺便付给我。 我上哪儿都不为收款,只是路过。”(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在《规矩》中,一位城里长大的农场主无意间惹恼了他的一名雇工。 “出什么事啦?” “你刚才说的话。”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说我们得使把劲。” “使劲儿堆草?——因为天快下雨? 我说这话至少是在半小时以前。 我那么说也是在为我自己加劲儿。” “你不懂行。但詹姆斯也是个傻蛋。 他以为你在暗示说他干活不卖力, 一般主人喊加油干都有那种意思。”…… “他要那样理解,那他真是个傻瓜。” “别为这事心烦。你已学到点东西。 对懂行的雇工有两个要求莫提—— 一是叫干得快点,二是叫干得好些……”(曹明伦先生的译文) 写城里长大的农场主的无知不是为了责怪他,而是为了赞扬将某样东西引以为豪的自尊。在弗罗斯特认为最好的品质中,自尊仅次于勇气。引以为豪的可能是一个人的技能,造斧人巴普蒂斯特的那种自豪;还有由于年老干不了活伤心而死的那个雇工,他曾为有堆干草的一技之长而自豪,使他不至于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又或者是在世人看来是蠢行的自豪,就像那个当不好农场主就烧了房子骗取保险赔偿的人,将到手的钱买了一个望远镜,又在铁路上找了一份身份低微的售票员的工作。那望远镜质量不好,那人很穷,但他觉得快乐,为他的望远镜感到自豪。 任何诗人都既是他所属文化的代表,又是这种文化的评论者。弗罗斯特没有写过讽刺诗,原因不难猜测,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他的同胞,是既认同又不认同。一般美国人隐忍克制,跟外人往往从他们无拘无束的友善态度得出的结论相反,他们轻易不说心事,比一般的英国人更不轻易流露感情。他们相信独立自主,因为不得不如此;生活太漂泊无定,环境变化太快,导致家庭或社会关系不能为他们提供固定的支撑框架。危急时他们会帮助邻居,无论邻居是什么人,但是他们会把经常来求助的看作坏邻居。他们看不起一切形式的自哀自怜和悔不当初的怀旧。所有这些品质在弗罗斯特的诗中都有反映,不过有些美国特性在他的诗中找不到,那意味着他不认同,比如那种认为找对了妙法就可以半个小时内建成人间天堂的信仰。我们可以把弗罗斯特形容为托利党人,前提是我们要记住所有美国政党都是辉格党。 我从不关心人生,人生关心我。 因此我欠了人生一些人情…… 投一冷眼 给生和死。 骑士,向前。 我希望我墓碑上写着的是 我跟人世闹过情人的别扭。 三首相比,毫无疑问是弗罗斯特完胜。哈代似乎是在说悲观主义者的情况,而不是他的真情实感。我从不关心……从不?少来了,哈代先生,说得跟真的似的!叶芝的骑士是一件舞台道具;过路人更有可能是开着汽车。但是弗罗斯特让我相信他说的是不折不扣的真我。而说到智慧,跟人世闹情人的别扭,难道不比不关心或投以冷眼更合乎普洛斯彼罗的身份吗?
译自TheDyer’’sHandAndOtherEssays,RandomHouse,NewYork,1962 译注:拔士巴原文是Bathsabe,应该是Bathsheba的异文。希伯来《圣经》中,拔士巴原是以色列国王大卫的一名大将的妻子,洗澡时被大卫看见,后来被大卫强占为妻。所以她并非少女,而是有夫之妇。奥登大概是看到嬷嬷,联想到莎士比亚的朱丽叶了。这有可能是一首题画诗(ekphrasis),奥登对它的评价未必允当。
来自群组: 读睡诗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