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阅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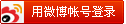
x
托马斯·哈代,英国诗人、小说家。哈代一生共发表了近20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等。哈代1840年出生于英国多塞特郡,1862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878年发表小说《还乡》,1891年发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1896年发表小说《无名的裘德》,《无名的裘德》中因为讲述男女主角是表亲的婚恋,导致哈代受到舆论攻击,自此哈代不再写作小说。晚年主要作品有三卷诗剧《列王》。1910年,哈代获得英国文学成就奖。哈代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晚年以其诗歌开拓了英国20世纪的文学。哈代创作诗8集,共918首,此外,还有许多以“威塞克斯故事”为总名的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史诗剧《列王》。
求爱于无生命者[1]
一
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英国批评家在一家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爱尔兰诗人谢默思·希尼的一部诗集[2];他指出,希尼在英国,尤其是在英国学术圈的知名度表明了英国公众迟钝的阅读品味,尽管艾略特和庞德两位先生的肉身在不列颠的土地上驻足多时,可现代主义却从未在英格兰扎根。他的看法的后一半让我很感兴趣(当然不是前一半,因为在那个国家,更不用说在那个圈子,人人都不愿别人好,恶意于是便成为一种保险策略),因为它听上去既发人深省又令人信服。
我很快就获得了与这位批评家见面的机会,尽管或许不该在饭桌旁谈论正事,但我还是向他提问,现代主义在他的国家为何如此不走运。他回答说,本该引导诗坛产生巨变的那一代诗人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觉得这个回答就其表达方式的性质而言似乎过于机械,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过于马克思主义化了,即过于夸大历史对文学的决定作用。但此人是一位批评家,而批评家就是这样工作的。
我认为还可以作出另一种解释,不是针对现代主义在大西洋彼岸的命运,而更像是说明传统诗歌如今在那里为何依然兴旺。原因显然有很多,而且昭然若揭,我们甚至无须再作讨论。首先是写作或阅读容易记住的诗行带给人的纯粹快乐;其次,就是韵律和韵脚的纯语言学逻辑以及对它们的需求。但是如今,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曲里拐弯的,因此在那一刻,我只是想到,最终将诗歌从成为一个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就是好的韵脚。在那一刻,我的思想转向了托马斯·哈代。
也许,我的思想也并不那么曲里拐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也许,“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说法触动了我的记忆,我想起了托马斯·哈代的“两千年的弥撒,/我们走向了毒气。”(After two thousand years of mass/We've got as far as poisongas.)在这里,我的思想依然是直截了当的。也许,这些思想是由“现代主义”一词触动的?在这里……发现自己属于少数人,一位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并不会因此感到惊恐,尽管他或许会有些焦躁。如果可以将一个世纪比作一种政治制度,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化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就可定义为专制制度,即现代主义之专制。或更确切地说,就是打着现代主义旗号出现的全面专制。也许,我的思想转向了哈代,就是因为在此时,在十多年前,他开始被习惯性地称之为“前现代派”。
作为一个概念,“前现代派”具有相当的谄媚色彩,因为它暗示,被如此定义的人铺出了一条通向我们这个正义和幸福时代(就文体意义而言)的大路。这个说法也有一个缺陷,即它会强迫作者退休,把他推回过去,当然也同时向他提供一切相应的好处,即学者的研究兴趣,不过却剥夺了他的实际效应。过去时态就等于他的那块银表。
没有任何一种正统学说,尤其是新的正统学说,能具备后见之明的能力,现代主义也不例外。给托马斯·哈代加上这么一个修饰语,现代主义或许会因此受益,可哈代本人,我想,却一无所获。无论如何,这一定义都会引起误解,因为我想,哈代的诗歌作品与其说预示了现代诗歌的发展,不如说超越了这一进程,而且是大幅地超越。比如说,T.S.艾略特当年读的如果不是拉福格[3]而是哈代(我相信弗罗斯特正是这样做的),本世纪英语诗歌的历史,至少是英语诗歌的现状,就会显得更加有趣。仅举一个例子,即在艾略特需要一大把尘土来感受恐惧的地方,哈代仅需一小撮,如他在《雪莱的云雀》(Shelly's Skylark)一诗中所显示的那样。[4]
二
毫无疑问,这一切在你们听来太多争辩色彩了。此外,你们还会感到奇怪,不知你们面前这个人究竟在与谁争辩。的确,关于诗人托马斯·哈代的文献微不足道。有两三部研究著作,它们其实都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出来的专著。还有两三本关于他的传记,其中包括他的一部自传,虽说封面上署着他妻子的姓名。这些书都值得读,尤其是最后一本,如果你们相信(我希望你们相信)一位艺术家的生活一定包含有理解他创作的钥匙。你们如果持相反的看法,错过一些东西,你们也不会损失太大,因为我们还要在这里讨论他的创作。
我想,我所不赞同的做法,就是透过这位诗人的继任者们的棱镜来看待他。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这些继任者们表现出了对诗人哈代之存在的相对无知或绝对无知,尤其是在大西洋的此岸。关于诗人哈代的研究文献之稀缺,就既是这种无知的证据,也是这种无知在当下的反映。其次,就整体而言,透过小人物的棱镜来看待大人物,这样做不会有大的收获,无论这些小人物多么人多势众;我们的专业学科可不是天文学。不过,这里最主要的原因仍在于,小说家哈代的存在自一开始便遮蔽了人们的视线,我所知道的批评家全都无法抵御这样一种诱惑,即将小说家哈代与诗人哈代捆绑在一起,这样一来便注定会降低其诗作的意义,即便这仅仅因为,批评家自己使用的文字就不是诗歌。
因此,对于一位批评家而言,研究哈代作品的任务就会显得相当麻烦。首先,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活包含着理解其作品的钥匙,就像大家公认的那样,那么在哈代这里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哪一类作品?某一不幸事件是反映在这部小说还是那首诗里?会不会同时体现在小说和诗歌里呢?如果体现在小说里,那诗歌怎么办呢?如果反过来,又会如何?更何况,他总共留下了九部长篇小说和近千首诗作。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这其中的哪部作品是升华之体现呢?一个人如何能持续不断地升华到八十八岁的高龄呢?因为哈代一直到死都在写诗(他的最后一部、亦即第十部诗集是死后出版的)。人们是否应该在小说家和诗人之间真的划上一条界线?抑或,以自然母亲为榜样使两者合二为一是否更好呢?
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两者分开吧。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在这间教室里要做的事情。长话短说,观察一位诗人只能透过他自己诗作的棱镜,而不能借助其他任何棱镜。此外,从理论上讲,托马斯·哈代只做了二十六年的小说家。由于他在写小说时也一直写诗,人们可以说,他持续不断地做了六十年的诗人。至少,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里他始终是一位诗人。在他最后一部、在我看来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遭受冷遇之后,他便完全放弃了写小说,而将精力集中于诗歌创作。仅凭他后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他就足以被赋予一种诗人身份。毕竟,三十年是这一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工作年限,甚至是某些诗人一生的长度。
因此,让我们把自然母亲先放在一边。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诗人的诗作。或者换句话说,让我们记住,人类的创造与所有自然杰作一样都是有机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那些自然科学家的说法,它们也是大量选择的产物。你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两种归于自然的方式。一种是脱得只剩下裤衩,或是更进一步,把自己袒露给所谓的自然元素。这像是劳伦斯的手法,它在本世纪下半期为众多傻瓜所效仿,我要遗憾地对你们说,尤以我们这边的傻瓜居多。另一种方式则在下面四行诗中得到了绝佳体现,这几行诗的作者是伟大的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
自然就是罗马,罗马反映着自然, 我们看到它公民力量的形象, 在蓝色杂技场般的透明空气, 在旷野般的广场,在密林般的柱廊。[5]
我说了,曼德施塔姆是位俄国人。但这里的四行诗却很切题,因为奇怪的是,比起同为英国人的D.H.劳伦斯的任何文字,托马斯·哈代与这首诗更为契合。
好吧,现在我想与你们一起读一读哈代先生的几首诗,我希望这几首诗你们已经能背诵了。我们将逐行分析这些诗,目的不仅是激起你们对这位诗人的兴趣,同时也为了让你们看清在写作中出现的一个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堪比《物种起源》里描述的那个相似过程,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还要说它比后者还要出色,即便仅仅因为后者的最终结果是我们,而非哈代先生的诗作。因此,请允许我屈服于一个显然是达尔文式的、既符合逻辑又符合年代顺序的诱惑,来着重分析前面提到的那三十年间的诗作,也就是托马斯·哈代写于其后半个创作生涯(亦即本世纪内)的诗,这样,我们便将小说家哈代放在了一边。
三
托马斯·哈代生于一八四年,卒于一九二八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石匠,无力支持儿子完成系统的教育,便让他跟当地一名教堂建筑师做学徒。但他自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经典著作,并在闲暇时写作,直到三十四岁时因《远离尘嚣》获得成功,他才放弃之前的职业。这么一来,他始自一八七一年的文学生涯便可清晰地划分成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即维多利亚时期和现代时期,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恰好死于一九一年。我们知道这两个概念都是标签,可为了篇幅起见,我们仍将使用它们,以便我们能节省一些气力。我们不应在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上浪费太多时间;对我们这位诗人而言,“维多利亚”这个词首先意味着罗伯特·勃朗宁、马修·阿诺德、乔治·梅瑞迪斯、两位罗塞蒂[6]、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当然还有丁尼生,当然还有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和A.E.豪斯曼[7]。你们或许还可以加上查尔斯·达尔文本人、卡莱尔、迪斯雷利、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拉斯金、塞缪尔·巴特勒、瓦尔特·佩特。但是让我们到此为止,这已经能让你们获得一个总的印象,了解到我们这位诗人当时所面对的精神和风格参数,或曰压力。让我们从这份名单中除去红衣主教纽曼,因为我们这位诗人是一位生物决定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让我们也除去勃朗特姐妹、狄更斯、萨克雷、特洛勒普、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以及其他一些小说家,他们对哈代先生曾经有所影响——当后者是他们中的一员时,但此种影响后来便消失了,比如在哈代写作《黑暗中的画眉》(The Darkling Thrush)一诗时,此诗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首诗:
我倚靠着矮林的门, 严寒灰白如幽灵, 冬天的残渣暗淡了, 白天那只变弱的眼睛。 缠绕的藤蔓茎秆探向天空, 就像被毁竖琴的琴弦, 在附近出没的所有人类 都已潜回家中的火炉前。
大地那锐利的形状像是 世纪的尸体横陈, 云层就是它的墓室, 风在为它的死亡哭泣。 萌芽和降生的古老脉搏 皱缩得又硬又干, 地上的每一个精灵都没了热情, 像我。
突然有个声音响起, 在头顶的萧瑟细枝间—— 一曲饱含热情的晚祷, 唱出无尽的欢乐; 一只年老的画眉,憔悴瘦小, 蓬乱着浑身的羽毛, 决定就这样把它的灵魂 投向越来越浓的黑暗。
如此喜悦地鸣叫, 并无太多的理由, 远近的尘世万物间也未写明原因, 于是我想,它幸福的晚歌里 一定颤动着某种神圣的希望,它心知肚明, 我却一无所知。
I leant upon a coppice gate When Frost was spectre-grey, And Winter's dregs made desolate The weakening eye of day. The tangled bine-stems scored the sky Like strings of broken lyres, And all mankind that haunted nigh Had sought their household fires.
The land's sharp features seemed to be The Century's corpse outleant, His crypt the cloudy canopy, The wind his death-lament. The ancient pulse of germ and birth Was shrunken hard and dry, And every spirit upon earth Seemed fervourless as I.
At once a voice arose among The bleak twigs overhead In a full-hearted evensong Of joy illimited; An aged thrush, frail, gaunt, and small, In blast-beruffled plume, Had chosen thus to fling his soul Upon the growing gloom.
So little cause for carolings Of such ecstatic sound Was written on terrestrial things Afar or nigh around, That I could think there trembled through His happy good-night air Some blessed Hope, whereof he knew And I was unaware.
这里的三十二行诗尽管是托马斯·哈代诗作中被收入诗歌合集最多的一首,却不是他最典型的诗作,因为它过于流畅。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经常被收入合集,尽管除了其中的一行,实际上任何一位富有才华或洞见的人都能写出这样的诗。此类诗作在英语诗歌中并不罕见,尤其在上世纪末。这是一首十分流畅、十分透彻的诗;其叙述平滑,结构保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叙事谣曲;其情节清晰,十分连贯。换句话说,这里很少地道的哈代。那么此时恰是一个最好的时刻,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地道的哈代。
地道的哈代是这样一位诗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憎恶平滑的诗行”。要不是因为在他之前那六百年的诗风,要不是因为像丁尼生一样的诗人对他虎视眈眈,此话听起来会有些古怪。说到这一点,他的态度其实与霍普金斯相差不大,我还想说,他俩表达这一态度的方式也差异很小。无论如何,托马斯·哈代的确主要是这样一位诗人,他的诗行拥挤紧绷,充满相互碰撞的辅音和张着大嘴的元音;他的句法十分复杂,冗长的句式因为其貌似随意的用词而愈显艰涩,他的诗节设计令读者的眼睛、耳朵和意识均无所适从,其从不重复的样式前无古人。
“那您干吗还要把他硬塞给我们呢?”你们会问。因为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的,从本世纪后来那些年间英语诗歌发生的变化来看,他的诗也是极富先兆的。首先,哈代诗句那种蓄意为之的笨拙并不仅仅是一位新诗人为谋求独特风格而作出的努力,尽管这一愿望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种表面的粗糙也不应仅仅被视为对后浪漫主义诗人那种音调上的高昂与优雅的反叛。实际上,后浪漫主义诗人的这些特性相当令人钦佩,说哈代或其他任何人“反叛”后浪漫主义诗人,对于这样的命题我们应当持保留态度,如果不是全盘否定的话。我认为,要解释哈代的语言风格,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为切实、同时也更为形而上的解释,而哈代的诗语风格自身便是既现实又形而上的。
形而上学永远是现实的,难道不是吗?形而上学越是现实,它就越是形而上,因为世间万物及其相互关系均是形而上学的最后的边疆:它们就是物质借以体现自我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句法的确十分复杂。我认为,哈代在其诗歌中所追求的很有可能就是用他的语言产生一种逼真的效果,一种真实的感觉,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可信的感觉。他大约认为,语言越粗糙,听起来就越真实。或者至少,语言越少雕琢,就越是真实。在这里,我们或许应该记起他还是一位小说家,虽说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提及他的这一身份。小说家们都会考虑这类事情,是吗?或者,让我们来一种更富戏剧感的表达:哈代曾是一位考虑这类事情的人,他因此才成了小说家。不过,这个成了小说家的人在此前和此后却是一位诗人。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了某些对于我们理解诗人哈代而言相当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此刻,你们恐怕只能暂且接受我的评价,但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哈代的诗句能够佐证这一看法。那我们就开始吧。我认为,托马斯·哈代是一个极具感知能力的狡黠之人。我在这里所用的“狡黠”一词并无负面含义,但或许我最好还是用“心思缜密”一词。因为他的确在缜密地构思他的诗作,不是作为一部小说来设计,而是完完全全作为诗作来构思。换句话说,他自一开始就明白一首诗会是什么样子,它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模样,他也准确地知道他的诗最终会有多少行。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可以相当精确地分解为呈示、展开和结局等不同部分,这与其说是因为它们的结构方式原本如此,不如说是因为结构能力对哈代而言就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源自他的内心,它所体现的与其说是他对当代诗歌潮流的熟悉,不如说是他对希腊和罗马经典作品的阅读,这对于那些自学成才者来说是屡见不鲜的。
他身上这种强大的结构本能也说明了哈代的风格为何从未有过发展,他的手法为何一直没有变化。如果不考虑主题,他的早期诗作可以很方便地置于其晚年诗集中,反过来也一样,他对于其诗作的写作时间和归集相当随意。此外,他最强的能力不是耳朵而是眼睛,我相信,在他看来,诗作的存在方式更像是印刷品而非朗诵对象。他如果朗诵自己的诗作,可能也会结结巴巴,但我不认为他会因此感到不好意思,并尝试加以改进。换句话说,对于他来说,诗歌的宝座就在他的思想中。无论他的某些诗作看上去多么像是面向人群,可它们与其说是真的在寻求公开朗诵,不如说是营造了一幅幅想象中的朗诵场景。即便他那些最为抒情的诗作,也只是对我们称之为诗歌抒情的东西作出了精神手势,它们更愿意紧贴在纸上,而不是运动于你们的唇间。很难想象哈代先生对着麦克风大声朗诵自己诗句的模样,不过我想,麦克风当时尚未发明出来。
好吧,你们或许还是会问我干吗要把他硬塞给你们。因为正是这种无声、这种听觉上的中立——如果你们愿意这么说的话,正是这种理智较之于情感的优势使哈代成了英语诗歌中的先知,这也正是后来的英语诗歌所热衷的。他的诗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传导出一种感觉,即它们在远离它们自己,似乎它们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在保持某种是诗的假象。这里就包含着一种新美学,这一美学强调艺术的传统手法,但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强调突出或自我声张,而是相反,是将它当做一种伪装,目的在于更好地融入艺术赖以存在的背景。这种美学拓展了艺术的范围,使得艺术能够以最出乎意料的时机和角度挥出更为有力的一击。这里正是现代主义出了差错的地方,不过过去的我们就让它过去吧。
然而,你们不能通过我的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哈代是块难啃的骨头。事实上,他的诗完全没有任何难解的奥秘。他诗中的独特之处自然就是他对无穷的强烈渴求,而传统手法的限制不仅没有束缚这一渴求,反而使它变得更加强烈了。不过,这些限制的确会束缚普通的、亦即非自我中心的智性,而无穷正是诗歌的标准领地。除此之外,作为诗人的哈代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命题,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哲学热身,你们便能欣赏他的诗。你们甚至可以称他为现实主义诗人,因为他的诗记录下了大量他所处时代的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我们可以大致将这种现实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
但你们不能将他称为维多利亚诗人。能使他摆脱这一定义的远不止他实际的生活年代;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前面说到的他对无穷的渴望,这同样也能使他摆脱除“诗人”外的任何定义。这个诗人要对你们谈一谈你们的生活,而他自己究竟生活在何时何地却不重要。当然,面对哈代,当你们道出“诗人”这个字眼时,你们眼前出现的不会是一个英俊潇洒、口若悬河的人,也不会是一位身患肺结核病的青年,在灵感袭来的迷狂状态中奋笔疾书,而是一个头脑清醒、日益冷峻的人,他秃顶,中等身材,留着小胡子,鹰钩鼻子,正坐在楼上的书房里,精心构思他那些虽说艰涩、却又冷酷的诗行,偶有所得,他便会发出笑声。
我之所以把他硬塞给你们,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这笑声。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十分现代的人物,这并不仅仅因为关于存在的真理在他诗行中所占的比例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而且还因为这些诗行所包含着的准确无误的自我意识。他的诗作似乎在对你们说:是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人工制品,因此我们不打算用我们的真理来诱惑你们,实际上,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听上去有些古怪。不过,姑娘和小伙儿们,如果你们觉得这位诗人很难啃,如果你们觉得他的语汇老掉牙了,你们一定要记住,问题或许不在于作者而在于你们自己。世上没有老掉牙的语汇,只有降低的词汇量。比如说,这就是百老汇如今不再上演莎士比亚剧目的原因,较之于环球剧场的戏迷们,如今的观众显然更难理解诗人莎士比亚的语汇。那么,这就是你们的进步了;最愚蠢的事情就是用进步的观点去回顾历史。现在,我们转向《黑暗中的画眉》。
四
当然,《黑暗中的画眉》是一首世纪末的诗。但是请假设一下,我们并未看到诗尾标明的写作日期;假设一下,我们打开一本书,偶然读到了这首诗。人们通常并不留意诗尾的日期,更何况,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哈代诗作的年代标注并不精确。因此,请想象一下,我们偶然读了这首诗,只在结尾处才看到写作年代。你们认为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
你们会说这是一首山水诗,是风景描写。你们会说,在一个寒冷、昏暗的冬日,有个人漫步于风景之中,时而驻足,记下他的所见。这是一幅凄冷的画面,但一只鸟的突然鸣叫却打破了这凄冷,这提振了他的精神。你们会这样说,你们的意见也是对的。此外,作者也恰好希望你们这么想,因为他的确在强调这一场景之寻常。
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你们最终明白,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时代,或是任何一种新的东西,全都开始于某个昏暗的日子,在这一天,你们精神不振,所见之处没有任何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太初并非有道,而有一个昏暗的日子[8]。(大约六年过后,你们就可以检验一下他的话是否正确了。)对于一首世纪末的诗作而言,《黑暗中的画眉》过于平淡,没有新千年的高调。这几乎与此诗标明的年代构成矛盾,这会使你们怀疑诗尾的写作年代是后加上去的,是后见之明。熟悉哈代的人很容易这么想,因为后见之明是他的强项。
不管怎样,让我们继续来看这首山水诗吧,让我们直接掉进他的陷阱。一切都开始于第一行的“矮林”(coppice)。他给出一个精确的植物类型名称,这会引起读者,尤其是现代读者的关注,这既体现了自然现象在说话人意识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同时也表明他很熟悉这些现象。这个词还在诗的开头制造出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因为一个知道灌木、篱笆和各种植物之名称的人,就其本性而言,几乎不可能是凶悍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行中听到的声音就是大自然盟友的声音,他的话语表明,这个自然很有可能是对人友善的。此外,他倚靠着矮林的门,这倚靠的姿势很少给人精神上的入侵感,如果说它富有某种含义的话,那也更像是接纳。更不用说“矮林的门”(coppice gate)本身就给出了一个相当文明化的自然,它已经习惯并几乎乐意让人通过。
第二行中的“灰白如幽灵”(spectre gray)原本或许会让我们警觉——如果不是因为四音步诗句和三音步诗句的正常交替及其民间谣曲般的余音的话(这种余音盖过了“幽灵”(spectre)一词中的鬼魂意味,竟然使得我们听到的词更像是“光谱”(spectrum)而非“幽灵”,我们的思绪随之飘向了色彩而非孤魂野鬼的王国)。我们在这一行里获得的感觉是一种被抑制的忧郁,而且它还奠定了全诗的韵律。在这里处于押韵位置的“灰白”(gray)一词其实释放了“幽暗”(spectre)中的两个e,像是发出了一声叹息。我们听到的是哀伤的eih,这与两个单词间的连字符一同,将“暗影”变成了一种色彩。
接下来的两行,即“冬天的残渣暗淡了/白天那只变弱的眼睛”(And Winter's dregs made desolate/The weakening eye of day),使这四行诗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这一结构方式贯穿着这首三十二行诗作的始终;我想,它也能让你们了解到这位诗人关于人类的某些总的看法,至少是他关于人类栖息地的看法。白天那只变弱的眼睛,大约是指太阳,它与这些冬天的残渣之间的距离使得后者不得不紧贴地面,呈现出“冬天”应有的白色,或者是灰色。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们这位诗人此处所见是几间乡村居所,我们在此看到的是一处山谷风景,这能让人忆起那个人间景象让星辰同悲的古老修辞。“残渣”(dregs)当然就是残余,就是喝完精华之后留在杯底的东西。此外,“冬天的残渣”(Winter's dregs)这个词组能让你们感觉到,这位诗人已毅然挣脱乔治诗风[9],两只脚都站在了二十世纪。
至少是一只脚,因为这首诗写于世纪之末。阅读哈代诗歌的另一个乐趣,就是能看到他所处时代的语汇(即传统语汇)和他自己的语汇(即现代语汇)始终在跳着双人舞。这两者在一首诗里相互摩擦,未来得以侵入现在,同时侵入了语言业已习惯的过去。在哈代这里,不同风格的摩擦如此醒目,这能使你们意识到,他不会紧紧抓住任何一种现代风格特征不放,尤其是他自己的现代风格。一行真正出新的、具有穿透力的诗行后面会跟着一连串老掉牙的东西,你们或许连它们的祖先都记不住了。作为例证,我们来看一看《黑暗中的画眉》第一节的后四行:
缠绕的藤蔓茎秆探向天空, 就像被毁竖琴的琴弦, 在附近出没的所有人类 都已潜回家中的火炉前。
第一行诗所具有的相对高级的意象(事实上与弗罗斯特的《柴堆》一诗的开头很相似),很快便退化为一个世纪之末[10]的明喻,即便在写作此诗的当时,这样的比喻也会散发出陈腐的赝品气味。我们这位诗人为何不在这里寻求一种更新鲜的语汇呢?他为何心满意足于这种十分维多利亚式,甚至华兹华斯式的比喻呢?他显然有超越他所处时代的能力,可他为何不作这样的尝试呢?
首先,因为诗歌尚未成为一项你死我活的竞争。其次,这首诗在此时尚处于呈示阶段。一首诗的呈示部是最奇特的部分,因为在这个阶段,诗人们大多尚不明白此诗接下来的走向。因此呈示部往往会很长,在英国诗人那里尤其如此,在十九世纪尤其如此。就总体而言,在大西洋彼岸,他们拥有更多的参考对象,而我们在这边则主要是参照我们自己。除此之外,再想想写诗的纯粹快感,想想将各种回声纳入诗节的快乐,你们便会意识到,某人“超越其时代”这样一种看法尽管不无赞誉色彩,实际上仍属后见之明。在第一节的后四行里,哈代显然是落后于其时代的,他丝毫不在意这一点。
事实上,他很喜欢这一点。这里的主要回声源于谣曲,“谣曲”(ballad)一词来自ballre,即舞蹈。这是哈代诗学的基石之一。应该有人来统计一下谣曲格律的作品在这位诗人创作中所占的比例,这极有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其说是年轻时的托马斯·哈代有在乡村集市上演奏小提琴的习惯,不如说是这位英国谣曲诗人迷恋血腥和惩罚,迷恋死神舞蹈[11]的特定氛围。谣曲调性的主要魅力恰恰就在于其舞蹈属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游戏属性,这种属性自一开始便彰显其狡黠。谣曲以及广义的谣曲格律会对读者说出这样的话:瞧,我并不完全是当真的。诗歌是一门十分古老的艺术,不可能不利用这一机会来展示其自我意识。换句话说,这一调性的无处不在不过是恰好吻合(“覆盖”是一个更佳的动词)了哈代的不可知论世界观,同时也论证了陈旧句式(“在附近出没”〈haunted nigh〉)或老套韵脚(“竖琴”/“火炉”〈lyres/fires〉)出现的合理性,除了一点:“竖琴”(lyres)一词会使我们注意到此诗的自指层面。
这一层面在下一诗节中充分体现了出来。这一节是呈示和主题叙述的结合。一个世纪的终结在这里被表现为一个人的死亡,这人似乎躺在那里供人吊唁。为了更好地赏析这一手法,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托马斯·哈代的另一门手艺,即他还是一名教堂建筑师。在这一点上,在将时间的尸体放进万物的教堂时,他采用了某种十分出色的技巧。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一技巧,这首先是因为他在那个世纪中生活了六十年。就某种意义而言,他同时拥有这座庞大的建筑和建筑内部的大部分内容。这双重的熟稔不仅来自特定季节的特定风景,而且来自他一贯的自我贬低——到了六十岁的年纪,这种自我贬低显得更加可信了。
萌芽和降生的古老脉搏 皱缩得又硬又干, 地上的每一个精灵 都没了热情,像我。
他的余生还有二十八年的时光(在这段余下的岁月中,他于七十四岁时再次结婚),这个事实并无任何意义,因为他不可能预知此类后事。一位好奇的读者甚至会紧盯着“皱缩得”(shrunken)一词不放,并在“萌芽和降生的脉搏”(pulse of germ and birth)中觉察到某种委婉的意味。不过,这或许既琐碎又牵强,因为这四句诗作出的精神姿态比任何个人的哀愁都要更宏大,更坚决。这四句诗以“我”(I)字结束,“没了热情”(fervourless)之后那个长长的停顿使“像我”(as I)两字显得尤为奇特。
呈示部到此结束,这首诗如果到此为止,我们也能得到一首好诗,一幅描绘大自然的速写,许多诗人的作品集里充斥的正是这样的诗。因为,许多诗作,尤其是自然主题的诗作,其实就是未能抵达其目标的被拉长的呈示部,它们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诗人从已完成的结构自身获得了愉悦。
此类事情在哈代身上从未发生。他似乎永远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愉悦对他而言既非原则亦非诗中的有效成分。他不太追求响亮的诗句,他诗行的排列相当松散,直到全诗中那具有冲击力的一行,或曰全诗的要点突然出现。因此,他的呈示部通常并不十分悦耳,如果有例外,就像在《黑暗中的画眉》中这样,那也更像是侥幸收获而非有意为之。在哈代这里,一首诗里的主要收获总是来自结尾。他通常会给你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诗句对于他来说只是交通方式,赋予其合理性、或许还有神圣感的仅为这首诗的目的地。他的耳朵很少好过他的眼睛,但他的耳朵和眼睛又都次于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强迫他的耳朵和眼睛服从他的思想,其态度有时还十分粗暴。
于是,此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绝对凄凉的画面:被各自的死亡结局所掌控的一个人和一片风景。下一诗节给出了关键:
突然有个声音响起, 在头顶的萧瑟细枝间—— 一曲饱含热情的晚祷, 唱出无尽的欢乐; 一只年老的画眉,憔悴瘦小, 蓬乱着浑身的羽毛, 决定就这样把它的灵魂 投向越来越浓的黑暗。
对于任何一位喜爱哈代的人来说,这段诗都是一座宝库。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首诗的主线,看看我们这位诗人想干什么。他想给你们指出一个出口,让你们步出上一诗节的死胡同。死胡同只能从上方越过,或是退回去。“响起”(arose)和“在头顶”(overhead)这两个词向你们说明了我们这位诗人所选定的路径。他在这里选择了全面的飞升;实际上,他选择了顿悟,带着鲜明的宗教内涵完全飞离了地面。但是,这次起飞的引人注目之处,却是与“一曲饱含热情的晚祷/唱出无尽的欢乐”(In a fullhearted eversong/Of joy illimited)一句的抒情释放如影相随的拘谨。这种拘谨你们在由“晚祷”(eversong)和“无尽的”(illimited)这两个词构成的长短格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两个词都以停顿开启,吐字仿佛一口呼出的气息;仿佛这些诗行开头还是断言,之后在他的喉头却消减成了修饰语。
这里所体现出的与其说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在诉诸宗教词汇时通常都会遭遇的难处,不如说是哈代本人真正的谦卑。换句话说,信仰的起飞在这里还受制于一种引力,即说话者尚不能确定他是否有权拥有这些飞升的手段。“一只年老的画眉,憔悴瘦小,/蓬乱着浑身的羽毛”(An aged thrush, frail, gaunt, and small, / In blastberuffled plume),这当然就是哈代的自画像。他那只众人皆知的鹰钩鼻子以及秃顶上翘着的一簇头发,的确使他看上去像一只鸟,尤其在他上了年纪之后。(“憔悴”〈gaunt〉是他十分钟爱的一个词,是他真正的签名,即便这仅仅因为这个词完全不具乔治诗派的味道。)
无论如何,这里的这只鸟除了举止很像诗人外,还具有诗人的五官特征。这就是我们这位诗人获得的一张通往鸟类情感世界的门票,由此便产生出了二十世纪英语诗歌中最伟大的诗句之一。
原来,这只外貌并不十分诱人的年老画眉
决定就这样把它的灵魂 投向越来越浓的黑暗。
说到用词方面的选择,没有比这里的“投向”(fling)更好的字眼了。考虑到鸟和诗人之间暗含的相似,这两行诗所表达的便既是鸟儿面对现实的姿势,也是诗人面对现实的态度。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这种态度的哲学基础下个定义,最终我们无疑会在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之间举棋不定。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而言术语学并非一个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必须把这两行诗吸收进我们的体系中——比如说,为一年中的黑暗时光构建的体系。
这首诗如果在这里戛然而止,我们也能获得一则非凡的道德训诫。这样的事情在诗歌中很罕见,但的确存在。此外,动物王国(尤其是鸟类王国)在诗歌中的优越性也由来已久。事实上,信奉这一优越性的观念就是诗歌最独特的饰物之一。《黑暗中的画眉》中十分突出的一点就是,诗人其实在与这一观念抗争;他先接受了这个观念,随后却又试图在这首诗的发展过程中将其抛售。不仅如此,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几乎就是在抗争自己最为成功的诗行。他的目的何在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这很难说清,也许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成功,他对形而上的热衷妨碍了他意识到这一点。关于他为何要在这里继续写作第四段,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与他的这种热衷相近的对称感。有些诗人爱写富有形式感的诗作,他们总是认为四段八行诗要胜过三段八行诗;我们不要忘记,哈代还是一位教堂建筑师。四行诗节就像是音调上的建筑砖石。作为建筑材料,它们会生出一种秩序,这一秩序被分成四份时最为和谐。对于我们这位诗人的耳朵和眼睛而言,十六行的呈示部自然要求此诗余下的部分至少也要拥有同样数目的诗行。
更客观地说,一首诗所运用的诗节结构在决定此诗的长度方面不亚于诗歌的叙事情节,甚至有可能超越后者。“如此喜悦地鸣叫 /并无太多的理由”(So little cause for carolings/Of such ecstatic sound)一句既是结局,也是对前面二十四行诗不得不作出的一个音调上的呼应。换句话说,一首诗的长度即它的呼吸。第一节是吸气,第二节是吐气,第三节是吸气……你们猜一猜第四节目的何在?就是为了完成这一循环。
请记住,这是一首以展望未来为主题的诗。因此,它必须保持平衡。我们这位主人公虽然是个诗人,却并非乌托邦主义者,他也不能允许自己摆出一副先知或预言家的姿态。主题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内涵十分含混,因此便需要诗人在此表现出清醒,无论他就性格而言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由此而来的便是第四诗节那绝对出色的语言内涵,以及法律术语(“理由……写明原因”〈cause…Was written〉)、现代派的超然(“尘世万物间”〈on terrestrial things〉)和典雅的古词(“远近”〈Afar or nigh around〉)这三者的混成。
“如此喜悦地鸣叫/并无太多的理由,/远近的尘世万物间/也未写明原因”(So little cause for carolings / Of such ecstatic sound / Was written on terrestrial things / Afar or nigh around),这一句所流露的与其说是我们这位诗人的格外乖张,不如说是他对于他在一首诗中使用的所有层级的风格用语的不偏不倚。哈代对于诗学的总的态度中含有某种吓人的民主意味,这可以归结为“有用便好”。
请注意这一节的哀歌式开头,前一行中“越来越浓的黑暗”(growing gloom)使得这一特质更加鲜明。音调仍在不断提高,我们仍在寻求飞升,寻求步出死胡同。“如此喜悦地”——停顿——“鸣叫/并无太多的”——停顿——“理由……”。“喜悦”(ecstatic)一词道出一声惊叹,恰如停顿之后的“鸣叫”(sound)。
就声响层面而言,此为这一诗节的最高点,甚至连结尾的“它心知肚明,/我却一无所知”(whereof he knew/And I was unaware)都要低几个调性,低几个阶梯。但我们看到,即便在这个最高点上,这位诗人也依然在控制他的声音,因为“如此喜悦地鸣叫”是“无忧无虑的晚祷”(a fullhearted eversong)的降调之结果。换句话说,对鸟儿声音的描写降了级,世俗语汇替代了宗教语汇。于是出现了这句可怕的“尘世万物间/也未写明原因”(Was written on terrestrial things),其中那种脱离任何具体事物的超然似乎表明了某种俯瞰的高度——它也许属于“白天那只变弱的眼睛”(weakening eye of day),或者至少属于那只鸟,因此,我们接下来便看到了这个古色古香的、也可以说是非个性化的“远近”(afar or nigh around)。
但是,这里的非具体化和非个性化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而属于这两者的融合体,而熔炉就是这位诗人的大脑,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就是语言本身。让我们更仔细地讨论一下这十分独特的“尘世万物间/也未写明原因”(Was written on terrestrial things)一句,因为它从一个此前并无任何一位诗人到过的地方悄悄潜入了这首世纪之交的诗作。
“尘世万物”(terrestrial things)这个词组表明一种非人类性质的超然。通过两个抽象概念的接近在此获得的这一视点,严格地说是无生命的。证明它属于人类创造的唯一证据是,它的确是“写出来”的。这会使你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语言能够作出如此排布,最终将人类贬谪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抄书吏。是语言在使用人类,而不是相反。语言自非人类真理和从属性的王国流入人类世界,它归根结底是无生命物质发出的声音,而诗歌只是其不时发出的潺潺水声之记录。
我绝对不是说,托马斯·哈代在这行诗里想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更有可能的是,这行诗想通过托马斯·哈代来表达这个意思,而他答应了。他似乎对自己笔下流出的文字感到有些困惑,于是便试图抑制这一感觉,其方式就是使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常用的语汇“远近”。但是,这个词组却注定会成为二十世纪诗歌的语汇,其影响越来越明显。从“尘世万物”到奥登的“必要的凶杀”(necessary murder)和“人工的荒芜”(artificial wilderness)[12]仅相隔二三十年。仅仅由于“尘世万物”这一句,《黑暗中的画眉》便可被视为一首世纪之初的诗。
哈代对这一词组的无生命声音作出了应答,这个事实显然表明他对谛听此类声音做好了充分准备,这并非因为他的不可知论(这个理由或许也很充分),而是因为每一首诗实际具有的上升矢量,即它对顿悟的追求。从原则上讲,一首诗在一张纸上向下蔓延,也就意味着它在精神上向上腾升,《黑暗中的画眉》就完全符合这一原则。在这一过程中,非理性并非障碍,这首谣曲的四音步和三音步格律就显示出某种十分近似非理性的东西:
于是我想,它幸福的 晚歌里一定颤动着某种 神圣的希望,它心知肚明, 我却一无所知。
让我们这位作者走近“神圣的希望”(blessed Hope)的,首先就是在三十行交替出现的四音步和三音步诗行中不断积累的那股离心力,它既要求声音上的结局,也要求精神上的结局,或是两者的合二为一。就这一意义而言,这首写于世纪之初的诗作所诉说的就是它自己,就是它自己的构成,幸运的是,这种构成也和十九世纪一样正在走向其结局。实际上,一首诗给了新世纪一个它自己的、关于未来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未必理性——以此使这个世纪成为可能。抗拒一切障碍,抗拒“理由”的缺失。
而这个新世纪——它很快也要结束了,对这首诗也回报甚多,就像我们在这间教室里所看到的这样。无论如何,就预言来说,《黑暗中的画眉》就比,比如说,叶芝的《第二次降临》更为清醒,也更加准确。画眉比雄鹰更可信[13],这或许因为,这只画眉出现在哈代先生面前的时间要早二十年;又或许因为,单调比尖叫更能呼应时间自身的话语。
因此,如果说《黑暗中的画眉》是一首关于自然的诗,那也仅能说它只有一半是,因为诗人和鸟儿均为自然之产物,而这两者间只有一个,用通俗的话说,还心存指望。这首诗的内涵更像是对于同一现实的两种接受态度,因此这显然是一首哲理抒情诗。希望和无望显然被公平地置于此诗,两者间并无等级差异,这两种情感的承载者则显然存在差异,我想指出,我们这只画眉是“年老的”(aged),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它见多识广,它那“神圣的希望”与希望的缺失同样合理。最后一行中将“一无所知”(unaware)孤立出来的那个停顿十分有力,足以使我们的遗憾噤声,并赋予最后一个单词以一种坚定的意味。毕竟,“神圣的希望”是面对未来的的,因此,这里的最后一个单词便是由理性道出的。
五
十二年之后,但依然在那位爱尔兰诗人的野兽动身前往伯利恒之前[14],英国邮轮泰坦尼克号在处女航中因撞上冰山而沉没在大西洋中。一千五百余人遇难。这大约就是被托马斯·哈代的画眉引来的这个世纪中诸多灾难中的第一桩,这个世纪也将因为这些灾难而臭名昭著。
《两者相会》(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ain)就写于这场灾难发生两周之后,然后又很快在五月十四日发表出来。泰坦尼克号是四月十四日沉没的。换句话说,关于这场灾难之原因的激烈争论,对航运公司的司法调查,幸存者的可怕叙述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首诗的写作之后。因此,这首诗可被视为我们这位诗人的一种本能反应。此外,此诗首次发表时还有一个副标题,即《泰坦尼克号失事有感》(Improvised on the Loss of the Titanic)。
那么,这一灾难究竟触动了哈代先生的哪根心弦呢?职业批评家们通常认为,《两者相会》是诗人哈代对现代人那种认为技术万能的自我欺骗发出的谴责,或是一曲哀叹人类因过分虚荣、追求奢华而遭报应的悲歌。确切地说,这两个主题在这首诗中并存。泰坦尼克号本身就既是现代造船业的一个奇迹,也是现代人浮华虚荣的突出体现。不过,我们这位诗人对冰山的兴趣似乎并不亚于邮轮。恰恰是冰山的形状,即锥体,预示了此诗的诗节构造。对于此诗的内容而言,“冰的形状”(A Shape of Ice)之无生命的本质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锥体也会让人联想到船,因为这也是帆的标准形态。此外,考虑到我们这位诗人曾做过建筑师,这一形状于他而言可能还暗指教堂建筑或金字塔。(毕竟,每一场悲剧都会制造出一个谜。)在诗中,这座金字塔的基座就是六音步诗行,诗行中间的停顿又将这六音步划分为两个三音步,这实际上是能够使用的最长音步,哈代先生十分偏爱这种音步,或许是因为他自学了希腊语。
虽说他对具象诗(它自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诗歌流传至今)的偏爱不应被估计过高,但他在诗节结构规则方面的用心仍足以使他意识到其诗的视觉维度,并作出相应的选择。无论如何,《两者相会》的诗节设计显然是有意为之的,它由两个三音步诗行和一个六音步诗行(在英语中通常恰好由两个三音步构成,这也是一种“两者相会”)构成,将它们连接为一体的是行末的三联韵。
一
在大海的孤寂中, 在远离人类虚妄的深处, 远离将她塑造的生命的骄傲,她静静躺卧。
二
钢铁的炉腔,先前是柴堆, 燃烧着她火蜥蜴的烈焰, 冰冷的水流穿过,将它变成潮水的悦耳竖琴。
三
一张张镜面上, 原本映着达官显贵, 如今海蛆蠕动,丑陋黏滑,无声冷漠。
四
博取欢乐的珠宝 本为刺激感官, 如今黯然静卧,所有的光泽都已消逝。
五
双目圆睁的鱼儿在近旁 凝视镀金的齿轮, 它们问:“这自负的家伙在这里干吗?”
六
这个嘛:在为这造物 装上劈波斩浪的翅膀时, 那无处不在的意志,操控一切
七
为如此喜气洋洋的她, 选中一个不祥的伴侣, 冰的形状,在另一个遥远的时间。
八
漂亮的轮船长大了, 亭亭玉立,花容月貌, 冰山在朦胧寂静的远方也已长大。
九
它俩看上去毫不相干, 凡人的眼睛无法预见 它们在后来会如此地亲密无间,
十
也看不出征兆,他们 注定会在路上相遇, 之后成为命定大事的双方,
十一
直到岁月的纺者说“时辰到!”, 每一个人都听到, 两人完婚,两个半球都被震惊。
I In a solitude of the seaDeep from human vanity,And the Pride of Life that planned her, stilly couches she.IISteel chambers, late the pyresOf her salamandrine fires,Cold currents thrid, and turn to rhythmic tidal lyres.IIIOver the mirrors meantTo glass the opulentThe sea worm crawls — grotesque, slimed, dumb, indifferent.IVJewels in joy designedTo ravish the sensuous mindLie lightless, all their sparkles bleared and black and blind.VDim mooneyed fishes nearGaze at the gilded gearAnd query:“What does this vaingloriousness down here?”VIWell:while was fashioningThis creature of cleaving wing,The Immanent Will that stirs and urges everythingVIIPrepared a sinister mateFor her — so gaily great —A Shape of Ice, for the time far and dissociate.VIIIAnd as the smart ship grewIn stature, grace, and hueIn shadowy silent distance grew the Iceberg too.IXAlien they seemed to be:No mortal eye could seeThe intimate welding of their later history,XOr sign that they were bentBy paths coincidentOn being anon twin halves of one august event,XITill the Spinner of the YearsSaid“Now!”And each one hears,And consummation comes, and jars two hemispheres.
你们看到的的确是一首公开信形式的应景诗。实际上,这是一篇演讲词,它会使你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它似乎是从讲台上传出的布道。开头一行,即“在大海的孤寂中”(In a solitude of the sea),无论在听觉还是视觉上都十分开阔,它在暗示海上天际线的宽广以及自然元素的自治程度——这种自治状态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孤寂。
但是,如果说第一行诗是在扫描宽广的表面,那么第二行诗,即“在远离人类虚妄的深处”(Deep from human vanity),却把你们更远地带离人类世界,径直带入这一绝对孤立的自然元素之内心。第二行诗实际上是一份邀请,邀请你们去进行一次水下之旅,全诗的前半部分(又是一个漫长的呈示部!)本质就在于此。到第三行诗的末尾,读者已经投入了真正的潜水探险。
三音步是个棘手的东西。它在声音方面或许很有效果,但自然会对内容有所约束。在这首诗开始的时候,它帮助我们这位诗人建立了他的调性,但他却急于展开这首诗的主题。为着这一目的,他写出了第三行。这是一行容量相当大的六音步,他在这行诗里的确采用了一种直奔主题的急性子方式:
远离将她塑造的生命的骄傲,她静静躺卧。
这一行诗前半段的突出之处在于其重音的累积,同样也在于它引入的东西,即那个夸张的抽象概念,而且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生命的骄傲”(the Pride of Life)在句法上自然是与“人类虚妄”(human vanity)联系在一起的,但单凭这一点却于事无补,因为首先,“人类虚妄”这个词组没有大写;其次,较之于“生命的骄傲”,它在观念上仍显得更为直白、耳熟一些。接下来,“将她塑造的”(that planned her)这一词组中的两个n会使你们产生一种话语被卡在瓶颈的感觉,这种词汇似乎更适宜于一篇社论而非一首诗。
没有任何一位深思熟虑的诗人会试图将所有这一切都置入半行诗中,因为这几乎完全无法诵读。另一方面,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当时还没有麦克风。实际上,“远离将她塑造的生命的骄傲”(And the Pride of Life that planned her)一句尽管有韵律显得机械之危险,却仍然可以大声读出来,甚至会造成某种略有些错位的重音效果,不过这显然需要付出一番努力。问题在于,托马斯·哈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答案就是,因为他相信,那艘沉入海底的轮船的意象以及他的三联韵将拯救这一诗节。
“她静静躺卧”(stilly couches she)则的确是对此行前半段重音累积的一种出色的再平衡。“静静”(stilly)一词中的两个l,作为一个“流质”的辅音,几乎能让人感觉到那艘船轻微摆动的船身。而韵脚则强化了这艘船的女性特征,这一特征已在“躺卧”(couches)一词中得到强调。对于这首诗的目的来说,这一提示的确非常及时。
在这一诗节中,首先是在这一诗节的第三行,我们这位诗人的举止能让我们对他产生什么印象呢?能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至少他很善于计算他的重音)。此外,左右诗人之笔的与其说是一种和谐感,不如说是他的一个中心思想,他的三联韵首先是一种结构工具,其次才是一种音调上的要求。至于韵脚,它在这一诗节中尚未令我们感到十分震惊。这一诗节最好的东西就是其高度的功能性,它与一首十五世纪的出色诗作构成呼应,后者曾被归在邓巴[15]的名下:
无论我生活在哪一阶层, 死亡的恐惧在折磨我…… “所有的基督徒们,你们看: 这个世界只是虚妄, 它充满着种种必然。 死亡的恐惧在折磨我。”
In what estate so ever I beTimor mortis conturbat me ... “All Christian people, behold and see: This world is but a vanity And replete with necessity. Timor mortis conturbat me.”
很有可能,这几行诗的确就是《两者相会》一诗的写作动机,因为这首先是一首关于虚妄和必然的诗,同样也自然是一首关于死亡之恐惧的诗。不过在《两者相会》中,令七十二岁的托马斯·哈代感到不安的恰恰是必然:
钢铁的炉腔,先前是柴堆, 燃烧着她火蜥蜴的烈焰, 冰冷的水流穿过,将它变成潮水的悦耳竖琴。
我们的确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水下旅程,尽管韵脚并不出色(我们又遇见了我们的老朋友“竖琴”〈lyres〉),可这一诗节的出众之处却在于其视觉内容。我们显然身在轮机舱,整台机器在海水的折射中微微颤动。这一诗节的出彩字眼其实是“火蜥蜴的”(salamandrine)一词。除了其神话学和冶金学方面的内涵之外[16],这个四音节的、蜥蜴般的修饰语还能奇妙地让人想起与水截然相对的另一种物质,即火。火熄灭了,却似乎在折射的维系下继续燃烧。
在“冰冷的水流穿过,将它变成潮水的悦耳竖琴”(Cold currents thrid, and turn to rhythmic lyres)一句中,“冰冷的”(cold)一词使这种转化显得更为突出。但就整体而言,这行诗之所以十分有趣,却是因为它似乎含有一个关于此诗创作过程的隐喻。表面上,更确切地说是在表面下,我们看到了波浪涌向海岸(或海湾)的运动,后者看上去就像是竖琴的琴身。因此,波浪便成了被拨动的琴弦。动词“穿过”(thrid)是thread的古体(或方言体),它不仅将声响和意义的织物从一行传至另一行,同时还在音调上让人意识到这一诗节的三角形设计,即一段三联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从“烈焰”(fire)到“冰冷”(cold)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能显示出普遍意义上的艺术家自觉意识的手法,考虑到此诗所体现出的面对大悲剧的处理方式,这更能暴露出哈代的自觉意识。因为直率地说,《两者相会》缺乏“热烈的”情感;考虑到遇难者的数量,在这里表露出这样的情感似乎是合适的。而这却是一首地地道道的非感伤诗作,在第二诗节,我们这位诗人暴露出了(很可能是无意之间)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一张张镜面上, 原本映着达官显贵, 如今海蛆蠕动,丑陋黏滑,无声冷漠。
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一诗节,此诗才获得了社会批判诗作的名声。这里自然有社会批判成分,但它却是最次要的一点。泰坦尼克号的确是一座漂浮的宫殿。舞厅、赌场、客舱本身就是穷奢极欲之体现,它们的装潢富丽堂皇。为了传达出这一点,诗人使用了动词“映着”(to glass),这个动词既可使奢华翻番,同时却也泄露出了奢华的单维性:它浅薄如镜面。不过我认为,在哈代先生描绘的这个画面中,他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戳穿富人的假面,不如说是揭示目的和结果之间的差距。海蛆在镜面上蠕动,这里所体现的并非资本主义的实质,而是“达官显贵”(the opulent)的对立面。
那一连串描写海蛆的负面修饰语向我们透露出了关于哈代先生本人的许多信息。因为,人们要想理解负面修饰语的价值,就永远要试着首先将它们用于自身。作为一位诗人,更不用说作为一位小说家了,托马斯·哈代可能不止一次这样干过。因此,这里的一连串负面修饰语就可以、也应该被看作是反映出了他对于人类之恶的等级划分,最深重的罪恶排在最后。而在这一行的最后,而且还处在押韵位置上的就是“冷漠”(indifferent)一词。这使得“丑陋”(grotesque)、“黏滑”(slimed)和“无声”(dumb)都成了次要的恶。至少在这位诗人看来是这样的。人们不禁会想,这一语境中对“冷漠”的谴责或许是指向诗人自己的。
博取欢乐的珠宝 本为刺激感官, 如今黯然静卧,所有的光泽都已消逝。
此刻或许是时候了,可以指出我们这位诗人在这里采用的这样一种一帧接着一帧的类似电影的手法,而且他如此行事是在一九一二年,远在电影成为每日的——更确切地说是每晚的——现实生活之前。我记得我在什么地方说过,发明蒙太奇手法的是诗歌,而非爱森斯坦。若干一模一样的诗节在同一张纸上的垂直排列就是一部电影。两三年前,一家试图打捞泰坦尼克号的公司曾在电视上播放了一段他们拍摄的沉船录像,那些镜头就很像我们在这里谈到的东西。他们看重的显然是船舱里的东西,其中可能还有约瑟夫·康拉德刚刚完成的一部小说的手稿[17],作者当时借助这艘邮轮把手稿寄给他的美国出版商,因为这艘船除了其他的长处外,还是一种速度最快的邮政运输工具。镜头不停地在船舱里来回绕圈,被各种财宝散发出的味道所吸引,却一无所获。托马斯·哈代的活儿却要出色得多。
“博取欢乐的珠宝”(Jewels in joy designed)一句中的两个j和两个s的确熠熠生辉。第二行(To ravish the sensuous mind)中三个嗖嗖作响、嘶嘶有声的s也是如此。不过,最佳的头韵用法还是出现在第三行(Lie lightless, all their sparkles bleared and black and blind),在这里,“刺激感官”的音调趋平,而诗行里所有的l均在“光泽”(sparkles)一词中劈啪爆裂,在“已消逝”(bleared and black and blind)处将珠宝变成了此行结尾时泛起的无数气泡。头韵就这样在我们的眼前自我消解了。
较之于在这一行里读出关于财富之短暂易逝的布道,更值得我们去做的就是去赞叹诗人的别出心裁。即便诗人的确想布道,他的重点也应该是悖论自身,而非社会评判。写作《两者相会》时的托马斯·哈代如果年轻五十岁,他或许会稍稍强化此诗的社会批评锋芒,虽说也未必一定如此。但他已经七十二岁,自己也衣食无忧。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丧生的一千五百人中还有他的两位熟人。但在他的水下旅程中,他并未去寻找那两个人:
双目圆睁的鱼儿在近旁 凝视镀金的齿轮, 它们问:“这自负的家伙在这里干吗?”
“凝视镀金的齿轮”(gaze at the gilded gear)显然纯粹由于头韵的惯性方才步入此节的第二行(作者在考虑上一个诗节的写法时也许曾想到其他一些词组,这个词组只是那些副产品之一),这一句描述了那艘轮船的华丽外表。这些鱼似乎游在舷窗之外,放大镜一般的效果就由此而来,它使鱼儿的眼睛大如圆月。但这一节里更为重要的却是第三句,它是整个呈示部的总结,是整首诗的主题思想之跳板。
“它们问:‘这自负的家伙在这里干吗?’”(And query:“What does this vaingloriousness down here?”)这一句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手法,全诗的其余部分都是在对这一行诗所提出的问题作答。最重要的是,它再度摆出了演讲的姿态,这一姿态先前由于过长的呈示部而有所弱化。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诗人在这里提高了他的用语层级,其方式就是将标准的法律术语“问”(query)与显而易见的教会词汇“自负”(vaingloriousness)用在一起。后一个单词五个音节的庞大身躯绝妙地令人联想到了那艘海底邮轮的巨大体积。但除此之外,无论是法律术语还是教会词汇,两者均清晰地表明了风格的转换以及整个视角的变换。
这个嘛:在为这造物 装上劈波斩浪的翅膀时, 那无处不在的意志操控一切, 为如此喜气洋洋的她, 选中一个不祥的伴侣, 冰的形状,在另一个遥远的时间。
这里的“这个嘛”(well)既是缓和,又是卷土重来的信号。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词汇,其目的首先在于让读者稍稍放松警惕,因为“自负”一词可能已经让他们产生了警觉;其次在于将更多的空气压入说话者的肺叶,因为他将展开一个内容丰富的冗长句式。这里的“这个嘛”与我们第四十任总统[18]的演说特性有些相似,它表明此诗的电影部分告一段落,严肃的讨论就此展开。看来,该诗的主题毕竟不是海底动物,而是哈代先生的因果观念,同时也是卢克莱修时代以降的诗歌自身的因果观念。
“这个嘛:在为这造物/装上劈波斩浪的翅膀时”(Well:while was fashioning/This creature of cleaving wing)告诉读者——首先是在句法上——我们始自很远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在“无处不在的意志”一句之前出现的从句将“轮船”(ship)一词在英语中的性别属性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三个女性意味越来越浓的单词,它们彼此间的亲近更给人以一种蓄意强调的感觉。“装上”(fashioning)原本可能就是一个完全中性的造船业词汇,如果它未被用来修饰具有某种宠爱色彩的“这造物”(this creature)一词的话;如果“这造物”后面没有紧接着“劈波斩浪”(cleaving)一词的话。在“劈波斩浪”一词中能听出的更像是“乳沟”(cleavage)而非“砍刀”(cleaver),它能表示船首破浪而行的运动,同时也能让人联想到刀片一般的白色风帆。无论如何,“劈波斩浪的翅膀”(cleaving wing),尤其是在这里处于韵脚位置的“翅膀”(wing)一词,使这一行诗升到了足够高的位置,哈代先生便可以在此引入他整个精神活动里的一个中心概念,即“那无处不在的意志操控一切”(The Immanent Will that stirs and urges everything)。
六音步充分展示出了这一概念宏大的怀疑论内涵。一个停顿以最自然的方式将固定词组与其修饰语分割开来,使我们得以充分体会“无处不在的意志”(Immanent Will)中那些辅音近乎雷鸣的回音,以及“操控一切”(that stirs and urges everything)中的坚定武断。由于此行在长短格上的有所保留——事实上,这种保留近乎犹豫,在“一切”(everything)一词中尤为明显——后一种感觉更为强烈。作为这一节中的第三行,这句诗充满了坚定不移的强大惯性,它会使你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整首诗都是为这一句而写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谈到哈代先生的哲学观点(假设我们真的可以谈论一位诗人的哲学观点的话——因为仅仅由于语言的全知天性这一点,这类讨论就注定是一种简化),就必定会承认,关于“无处不在的意志”之观念就是他的思想基石。这一切会使人回溯至叔本华,你们最好尽早看一看这位哲学家的书,与其说为了哈代先生,不如说为了你们自己。叔本华会让你们少走很多路,更确切地说,是他关于意志的观念能让你们少走很多路,他在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如你们所知,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极易被指称为实质上的唯我论,如果不是纯粹的拟人论的话。就整体而言它们莫不如此,这恰恰因为它们均为体系,因此便会体现出整体设计的那种程度不一,但往往是高度的理性。叔本华却由于其“意志”而摆脱了这种指称,他的这一概念指的是现象世界的内在本质,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非理性力量,一股控制这个世界的盲目、贪婪的势力,其操控并无终极目的或设计,亦非某位哲学家热衷的理性或道德秩序之体现。当然,归根结底,这一概念也可以被指称为人类的自我投射。但是,它却能比其他观念更好地为自身辩护,而它仰仗的便是其恐怖的、无意义的全知,这种全知渗透进了为存在而进行的一切斗争方式,可它的声音却只能借助诗歌发出(在叔本华看来,诗歌发出的只是它的回声)。对于无穷尽、无生命的一切深感兴趣的托马斯·哈代会关注这一概念,这并不奇怪;他在这一行诗中用大写字母标出“无处不在的意志”这一词组,这也并不奇怪,人们可能会觉得整首诗就是为了这一行而写的。
事实却并非如此:
为如此喜气洋洋的她, 选中一个不祥的伴侣, 冰的形状,在另一个遥远的时间。
如果你们给上一行标了四颗星,那么你们会如何对待“冰的形状,在另一个遥远的时间”(A Shape of Ice, for the time far and dissociate)这一行呢?或者,如何对待“不祥的伴侣”(sinister mate)呢?这些词组远远地走在了一九一二年之前!这简直就是奥登的诗句。这些诗句就是未来对现在的入侵,它们就是“无处不在的意志”之呼吸。对“伴侣”(mate)一词的选用绝对出彩,因为这除了能让人联想到“同船船员”(shipmate)一词外,它还再度强调了轮船的女性属性,接下来的三个音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即“为如此喜气洋洋的她”(For her — so gaily great —)。
我们在这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的并非是用碰撞来隐喻浪漫的结合,而是相反,即用结合来隐喻碰撞。邮轮的女性特征和冰山的男性特征已得以确立。不过这并非确指冰山。我们这位诗人之天赋的真正体现就在于他给出了这一委婉的说法,即“冰的形状”(A Shape of Ice)。其可怕的力量直接取决于读者凭借自身想象力的负面潜能来塑造这一形状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一委婉的说法,更确切地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字母a,便可使其读者成为这首诗的积极参与者。
实际上,“在另一个遥远的时间”(for the time far and dissociate)一句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不错,“遥远的”(far)作为时间的修饰语十分常见,任何一位诗人都可能这样写。但是,只有哈代能将完全没有诗意的“另一个”(dissociate)写入诗中。这要归功于我们前面提及的他那种总体上的冷漠风格。对于这位诗人来说,没有好词、坏词和中等的词之分,唯一重要的就是这些词能否发挥功能。这当然应该归功于他作为一位小说家的经验,如果不应归结为他对平滑的“珠宝诗行”的一贯嫌弃的话。
“另一个”一词的光彩有多么暗淡,它的功能就有多么强大。它不仅表示“无处不在的意志”之远见,而且还预示着时间自身的不连贯特征,并非莎士比亚意义上的,而是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亦即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世的。正是后者使每一位读者将自己等同于灾难的亲历者,将他或她置于时间的碎裂区域。当然,最终拯救了“另一个”一词的还是它押韵的尾音,而且它还在六音步的第三行里完成了格律上的二音节合一。
事实上,在上两个诗节里,韵脚的使用越来越好,因为它们显得引人入胜,出人意料。为了充分地欣赏“另一个”一词,或许应该尝试纵向地读一下这节诗的韵脚。你们会读到“mate — great — dissociate”。这足以让人颤抖,而且自有深意,因为早在这一节诗写出之前,这一组韵脚便显然已经潜入诗人的脑海。实际上,正是这组韵脚让诗人按照他的方式写出了这节诗。
漂亮的轮船长大了, 亭亭玉立,花容月貌, 冰山在朦胧寂静的远方也已长大。
原来,我们面对的是一对未婚夫妻。女性般的漂亮轮船早已许配给了“冰的形状”。人类产品许配给了自然。近乎黑发的女子许配给了金发的男子。在普利茅斯港湾长大的东西正扑向在北大西洋“朦胧寂静的远方”(In shadowy silent distance)长大的东西。这个悄静、诡秘的“朦胧寂静的远方”强调了这个讯息的隐秘特性,近乎机械地落在这一诗节每个单词头上的重音就是时间那从容脚步的回声,未婚妻和她的未婚夫就迈着这样的脚步在相互走近。因为,使这次相遇注定实现的因素并非两位青年男女的个人特征,而是这脚步。
使他们的接近不可避免的还有这一诗节的一组韵脚。“长大”(grew)悄悄潜入第三行,于是便使这三行诗包含着四个韵脚。当然,这个韵脚的效果或许是廉价的,如果不考虑它的音响的话。“grew — hue — too”在音调上会让人想到“你”(you),第二个“grew”会令读者意识到自己是故事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
它俩看上去毫不相干, 凡人的眼睛无法预见 它们在后来会如此地亲密无间,
在前四个诗节构成的声响语境中,“毫不相干”(alien)一词听起来就像是一声惊叹,它那两个敞开的元音就像是在劫难逃者在服从不可避免的厄运之前发出的最后呼喊。这就像是在断头台上喊出的“我无罪”,或是在教堂祭坛前道出的“我不爱他”,一张苍白的脸转向公众。的确是祭坛,因为第三行中的“亲密无间”(welding)和“后来”(history)听起来就像是“婚礼”(wedding)和“命运”(destiny)的同音同义词。因此,“凡人的眼睛无法预见”(No mortal eye could see),这与其说是诗人在炫耀自己对因果关系机制的了然,不如说是劳伦斯神甫[19]发出的声音。
也看不出征兆, 他们注定会在路上相遇, 之后成为命定大事的双方,
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一位诗人会敲榔头般地在一行诗中砸下如此之多的重音,除非他是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即便霍普金斯也不敢在诗中使用“之后”(anon)一词。莫非就是在这里,我们的老朋友哈代先生对平滑诗行的厌恶达到了乖戾的程度?或者这是一次更为大胆的尝试,用这个中古英语单词“anon”来取代当今的“at once”,借此来遮挡“凡人的眼睛”(mortal eye),使他们看不见诗人之所见?这是远景的拉长吗?是在寻求那些相交的溯源路径吗?是他对关于这场灾难的标准看法所作出的唯一让步?或者只是提高了声调,就像“命定”(august)一词所产生的效果,从全诗结尾的角度看,是为了给“无处不在的意志”的话语铺平道路。
直到岁月的纺者说“时辰到!”, 每一个人都听到, 两人完婚,两个半球都被震惊。
在“无处不在的意志”“操控”的“一切”之中,或许也包括时间。“无处不在的意志”因此获得一个新的名称,即“岁月的纺者”(Spinner of the Years)。对于一个抽象概念的抽象表达而言,这个说法有些过于拟人化,但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哈代的教堂建筑师的心理惯性。他在这里距离将无意义等同于恶意已经仅一步之遥,而叔本华则恰恰推崇那个意志盲目机械的、亦即非人的本质,其在场能被一切形式的存在所感知,无论是有生命的存在还是无生命的存在,其表现形式即压力、冲突、紧张以及灾难,就像这一事例。
归根结底,他的诗歌之所以时时处处充满对戏剧事件的偏爱,其奥秘正在于此。关于现象世界的终极真理之非人性点燃了他的想象,恰如女性之美能点燃许多登徒子的想象。另一方面,作为一位生物决定论者,他自然会热情接受叔本华的观念,这不仅因为这一观念在他看来就是完全无法预测的、无法用其他方法加以解释的一切事件之源头(从而将“另一个”与“遥远”统一起来),而且还由于,人们会猜想,它能为他本人的“冷漠”提供解释。
你们当然可以称他为一位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但这或许是个错误,因为“无处不在的意志”这一概念不能说是非理性的。不,结论或许正相反。这个概念非常令人不快,甚至或许是令人恐惧的。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舒适不应被等同于非理性,一如理性不应被等同于舒适。这不是一处挑错的地儿。有一件事情显而易见,即对于我们这位诗人而言,“无处不在的意志”具有“最高存在”之地位,近乎“原动者”。因此,它十分恰当地道出了一个单音节的词;同样恰当的是,它道出的那个词是:“时辰到!”(Now!)
不过,这最后一个诗节中最为恰当的词自然还是“完婚”(consummation),因为相撞发生在夜间。“完婚”一词使我们最终看到了一个关于婚礼的比喻。“震惊”(jars)会让人联想到打碎的陶器,这与其说是这比喻的扩展,不如说是比喻的残留。[20]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动词,它使得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原本打算将其联结起来的两个半球成了两个相撞的大肚容器。似乎,正是“处女”(maiden)的概念首先拨动了我们这位诗人的“竖琴”。
六
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就是哈代先生在《两者相会》一年后写作的一组诗,即著名的《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诗抄》(Poems of 1912—1913)。在我们打算对其中的一首展开讨论前,让我们不要忘记,那艘女性的轮船沉没了,而那块男性的“冰的形状”却在冲撞之后得以幸存。这种对感伤情调的全然舍弃(尽管感伤对于此诗的体裁和主题而言都是适宜的),可以归咎于我们这位诗人无法在此对沉没者产生认同,即便这仅仅由于轮船的女性特征。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诗抄》的写作因由是诗人三十八岁的妻子艾玛·拉维尼娅·吉福德的离世,她死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八个月之后。这组由二十一首诗构成的组诗,似乎就是“冰的形状”之融化。
长话短说,这场婚姻持续得很久,其不幸足以派生出《两者相会》一诗的核心隐喻。可这场婚姻也足够牢固,至少能使其当事一方意识到他是“无处不在的意志”之玩物,而且是一个冰冷的玩物。如果艾玛·哈代活得比她丈夫更久,那么,对于他俩彼此分离的生活所构成的阴郁平衡而言,对于这位诗人心灵之低温而言,这首诗都将成为一座引人注目的纪念碑,尽管是一座歪歪斜斜的纪念碑。
艾玛·哈代的突然离世打破了这种平衡。换句话说,“冰的形状”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了。再换句话说,《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诗抄》其实就是这座冰山唱给那艘沉船的一曲哀歌。这些诗作是对那场损失的审慎重构;很自然地,这与其说是关于悲剧起因的形而上学探究,不如说是痛苦自省的副产品。归根结底,损失是无法借助探明原因而获得补救的。
正因为如此,这组诗实际上是回溯性的。把长话说得再短一些,这组诗的女主人公并非艾玛·哈代,即一位妻子,而是先前的新娘艾玛·拉维尼娅·吉福德,即一位少女。这组诗透过婚后三十八年的棱镜看着她,透过艾玛·哈代自己那块朦胧坚硬的晶体看着她。如果说这组诗中有个男主人公,那么他就是往日的时光及其幸福,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往日的时光对幸福的许诺。
作为对人类窘境的描摹,这个故事相当平常。作为哀歌的主题,对逝去爱人的吟唱也同样很平常。使得《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诗抄》自一开始便显得有些非同一般的因素不仅是诗人及其女主人公的年龄,而且还有构成组诗的诗作数量以及它们形式上的多样。为凭吊某人故亡而作的哀歌通常都具有一个典型特征,即音调上的一致,至少是韵律上的一致。可是在这组诗中,韵律上的不一致却显而易见,这或许表明,对于诗人哈代而言,诗艺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主题本身。
当然,一种针对这种多样性的心理学解释或许就是,我们这位诗人的悲伤在寻求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不过,他在这方面进行的二十一次尝试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复杂性也表明,这组诗背后所隐藏的压力或许大于纯粹的悲伤,或者说大于任何一种单一情感。因此,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诗作中或许最少诗节设计的一首,来探一探其中的究竟。
你最后一次乘车
你归来时走了这条荒野之路,你看到了前方城里的灯火,灯火照亮你的脸庞,无人想到,一周后这却成了逝者的脸庞,你曾说起这光环中的迷人美景,它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眼前。你路过的道路左侧的墓园,八天后你竟将在那里长眠,成为人们口中的逝者;你心不在焉地看了那儿一眼,觉得与你无关,虽说在这树下你很快便将永久地逗留。我未与你同乘……如果那晚我坐在你身旁,我绝不会看到我抬眼瞥见的这张面庞,在闪烁光亮中现出临终的容颜,也不会读到你脸上的卜辞:“我很快就要去我的长眠之地;“你会想念我。但我不知道你会去那儿看我几次,你会有什么想法,或者,你是否从不去那儿。我不在乎。你若责备我,我不会留意,甚至不再需要你的赞美。”是的,你不会知道。你不会在乎。但我因此就会将你冷落?亲爱的鬼魂,你过去可曾发觉“这有何益”的想法左右过我?然而,这一事实已然存在:你已超越爱情和赞美,冷漠和责备。
YOUR LAST DRIVE
Here by the moorway you returned,And saw the borough lights aheadThat lit your face — all undiscernedTo be in a week the face of the dead,And you told of the charm of that haloed viewThat never again would beam on you.And on your left you passed the spotWhere eight days later you were to lie,And be spoken of as one who was not;Beholding it with a heedless eyeAs alien from you, though under its treeYou soon would halt everlastingly.I drove not with you ... Yet had I satAt your side that eve I should not have seenThat the countenance I was glancing atHad a lasttime look in the flickering sheen,Nor have read the writing upon your face,“I go hence soon to my restingplace;“You may miss me then. But I shall not knowHow many times you visit me there,Or what your thoughts are, or if you goThere never at all. And I shall not care.Should you censure me I shall take no heedAnd even your praises no more shall need.”True:never you'll know. And you will not mind.But shall I then slight you because of such?Dear ghost, in the past did you ever findThe thought “What profit”, move me much?Yet abides the fact, indeed, the same,—You are past love, praise, indifference, blame.
《你最后一次乘车》是组诗中的第二首,就其末尾标明的时间看,它写于艾玛·哈代死后一个月之内;也就是说,她的离去所造成的震撼尚未过去。从表面上看,此诗回顾她最后一次照例出门后在晚间归来,前两节是在探究运动和静止这两者相互作用的悖论。女主人公乘坐的马车驶过她不久将葬身的地方,这似乎激起了诗人的想象,这个隐喻既指运动对于静止的短视,亦指空间对于两者的漠视。无论如何,这两节的理性动机似乎大于情感动机,尽管后者率先出现。
更确切地说,此诗偏离情感步入理性,而且相当迅速。就这一意义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地道的哈代,因为他很少会在这一点上出现相反的倾向。此外,任何一首诗就其定义而言都是一种运输工具,这首诗尤其如此,因为它至少在韵律上像是在描述一种运输工具。四音步扬抑格,飘忽不定的停顿悄然使第五行成为扬扬抑格,这一诗节绝妙地传导出了马车颠簸起伏的运动方式,结尾的两行在模拟马车的抵近。就像在哈代的笔下注定会出现的那样,这一手法贯穿全诗。
我们首先看到了女主人公的五官,她的脸庞被“前方城里的灯火”(the borough lights ahead)映亮,灯火很可能是朦胧的。此处的灯火与其说是诗意的,不如说是电影式的,“城里”(borough)一词也没有将用词拔高,尽管女主人公的出场会让你们产生这样的预期。相反,这一行半诗都在强调——甚至带有同义反复的味道——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变成“逝者的脸庞”(the face of the dead)。实际上,她的五官是缺失的;我们这位诗人之所以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描绘她的五官,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组诗的前景他早已了然于胸(尽管没有一位诗人会断定自己能写出下一首诗来)。不过,她在这节诗得到体现的却是她的话语,在“你曾说起这光环中的迷人美景”(And you told of the charm of that haloed view)一句中能听到她话语的回声。人们能在这一行中听见她的感叹:“太迷人了。”或者是:“瞧这光环!”因为人人都说她是一位经常去教堂的女性。
第二节对“荒野之路”(moorway)地形的关注并不亚于对事件时间顺序的把握。看来,女主人公的外出发生在她去世前一周,或许还不到一周,她在第八天被葬在这个地方,这里显然在她乘车沿着荒野之路回家途中的左侧。这种一五一十的态度或许源于诗人有意驾驭其情感的愿望,“地方”(spot)一词显示出一种有意的降调。这无疑也与一辆缓缓行进的马车的构思相吻合,而支撑这辆马车的正是四音步的弹簧。不过,我们深知哈代喜好细节,喜好尘世,我们或许也可以假设,他在此并未作出任何特殊努力,并未谋求任何特殊意义。他只是在表达一场不可思议的巨变是如何以一种平淡无奇的方式发生的。
由此导出下一行,这是这一节的制高点。在“成为人们口中的逝者”(And be spoken of as one who was not)一句中,人们觉察到的感受与其说是失却或令人难以承受的缺席,不如说是吞噬一切的否定。“逝者”(one who was not)的说法对于安慰而言(或者对于不安而言也同样如此)过于斩钉截铁,而死亡正是对一个个体的否定。因此,“你心不在焉地看了那儿一眼,/觉得与你无关”(Beholding it with a heedless eye / As alien from you)便不是责怪,而更像是对得体反应之认可。到了“虽说在这树下/你很快便将永久地逗留”(though under its tree / You soon would halt everlastingly),那辆马车和这首诗的呈示部也的确停了下来。
实际上,这两节诗的中心主题是,女主人公对她即将来临的结局一无所知或曰毫无预感。她要是产生了这样的预感倒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年龄的话。此外,尽管诗人在他的这组诗里始终在强调艾玛·哈代的离世之突然,可通过其他材料我们得知,她患有多种疾病,其中包括精神失常。但是,她身上的某种特质似乎使他相信她会长寿;或许,这个想法与他关于自己是“无处不在的意志”之玩物的概念有关。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第三节的开头是悲伤和悔恨主题之预示(同样也是在这些人眼中,这一主题是贯穿整部组诗的),但“我未与你同乘”(I drove not with you)只是在复述预感到妻子亡故的前提条件;退一步讲,这至少是在复述他可能无法获得这样的预感。接下来的一行半相当坚决地论证了这种可能性,排除了说话者因此而自责的根据。但是在这里,真正的抒情首度潜入此诗:首先是借助省略号,其次是通过“如果那晚我/坐在你身旁,我绝不会看到”(Yet had I sat / At your side that eve)这一句(这一句当然是在说明她去世时他不在她身边)。在“我抬眼瞥见的这张面庞”(That the countenance I was glancing at)一句中,抒情的力量空前饱满,这里的“面庞”(countenance)一词中的每个元音都是颤动的,能让你们看到那位乘客的面部侧影,那侧影背衬着光亮,随着马车的运动左右摇摆。这又像是一种电影技法,而且是黑白电影。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用“闪烁光亮”(flickering[21])一词来强化这种感觉,如果这首诗不是写在一九一二年的话。
况且还有“现出临终的容颜”(Had a lasttime look)所包含的严酷(不过,感知往往走在技术的前面,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蒙太奇并非爱森斯坦的发明)。这种严酷语调既强化、同时也摧毁了“我抬眼瞥见的这张面庞”一句中近乎露出爱意的试探性语调,泄露了诗人急于由幻想逃往真理的愿望,似乎后者才更有价值。
幻想他是肯定要逃离的,但他付出的代价是奇特的下一行,即“也不会读到你脸上的卜辞”(Nor have read the writing upon your face)一句中对女主人公真实相貌的回忆。这里的“脸上的卜辞”(the writing upon your face)显然源自“不祥之兆”[22],后者与女主人公相貌无可避免的合二为一足以让我们了解到这场婚姻在她死亡之前的状态。预示出这种合二为一的就是他感觉到了她的难以理解,此诗到目前为止始终在围绕这一主题,因为这种难以理解既适用于未来,也同样适用于过去,而这正是她与未来共有的一种品质。因此,他在艾玛脸上读到的文字就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23],这并非想象。
“我很快就要去我的长眠之地; “你会想念我。但我不知道你会去那儿看我几次,你会有什么想法,或者,你是否从不去那儿。我不在乎。你若责备我,我不会留意,甚至不再需要你的赞美。”
这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公,每一个字都是。凭借巧妙组合的时态,这声音像是来自坟墓,也像是来自过去。它冷酷无情。她的每一句话都是对上一句的否定。她肯定和否定的显然都是他的人性。她以这种方式表明,她的确是诗人的好伴侣。在这些诗行中可以听到夫妻争吵的清晰回声,争吵的紧张性完全压倒了这些诗句的无精打采。那声音越来越高,盖过了马车车轮碾过鹅卵石地面发出的声响。毫不夸张地说,死去的艾玛·哈代仍能侵入她那位诗人的未来,他只好奋起自卫。
我们在这一节里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幽灵。虽说这组诗的题辞“旧爱遗迹”引自维吉尔,可这一节就其调性和内容而言却十分近似赛克斯图斯·普罗佩提乌斯的著名哀歌《肯提娅单卷本》。无论如何,此节的最后两行都像是在忠实地翻译肯提娅最后的请求:“至于你为我写的诗,请烧了它们,烧了它们!”
摆脱这种否定的唯一出路即逃向未来,我们这位诗人走的就是这条路:“是的,你不会知道。”(True:never you'll know.)不过,这未来似乎相当遥远,因为其可预见的部分,亦即诗人的现在,已经被占据。于是才会有“你不会在乎”(And you will not mind)和“但我因此就会将你冷落?”(But shall I then slight you because of such?)。在这逃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这最后一节的第一行,终于出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即意识到了最终的分离和不断增大的距离。哈代照例带着惊人的节制处理这一行,只让自己在停顿处叹息一下,在“在乎”(mind)一词上稍稍提高一点音调。但是,被压抑的抒情挣脱缰绳,在“亲爱的鬼魂”(dear ghost)处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的确是在称呼一个幽灵,但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幽灵。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甜美的称呼,仅仅这一点就能让人确信诗人使用的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他没有试图在此寻找一种委婉的替代说法。(又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呢?根据格律他在这里仅有两个音节可用,“亲爱的艾玛”〈Dear Emma〉被排除了,那么就用“亲爱的朋友”〈Dear Friend〉?)她的确是个鬼魂,这并非因为她死了,而是因为她虽然不再是个实体存在,却远远不止一份记忆:她是一个他可以与之说话的存在,一个他十分熟悉的在场者(或缺位者)。凝聚成这种物质的并非婚姻生活的惯性,而是时间的惯性——三十八年的时间;在他的感受中,他的未来愈发固化了这一物质,而未来不过是时间的另一项增量。
“亲爱的鬼魂”便由此而来。带有这一称谓的她几乎可以被触摸到。或者,“鬼魂”就是疏远的极致。对于一位阅尽两人之间的共同关系、从纯粹之爱走向最终冷漠的人而言,“鬼魂”一词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称之为附注和总结。“鬼魂”一词在这里的确具有某种发现和总结的意味,此诗接下来的两行其实就是一种总结:“然而,这一事实已然存在:/你已超越爱情和赞美,冷漠和责备。”(Yet abides the fact, indeed, the same,— /You are past love, praise, indifference, blame.)这里所描写的不仅仅是鬼魂的状态,而且还有诗人哈代所采取的一种新态度,这一态度贯穿着组诗《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诗抄》,没有这一态度,或许就不会有这一组诗。
全诗结尾处对四种态度的罗列,在策略上与《两者相会》中的“丑陋黏滑,无声冷漠”的用法十分相似。但是,尽管为相似的自我贬低的逻辑所驱动,这一罗列最终并未产生逻辑分析那种简化式的精确(“四中选一”),而是获得一个极其情感化的总结,这种情感总结重新定义了葬礼哀歌,也同样重新定义了爱情诗歌自身。粗粗一看,《你最后一次乘车》像是一首葬礼哀歌,但细读其结尾,却能感到这就是一则姗姗来迟、在诗歌中难得一遇的附注,附注的对象就是爱情意味着什么。递交这样一份总结显然是邀请鬼魂加入对话的最低要求,最后一行也就有了某种邀请式的,甚至是调情的意味。我们这位老人在向无生命者求爱。
七
每一位诗人都要从他自己赢得的突破中汲取经验;一贯倾向于“目不转睛地直面糟糕”的哈代,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诗抄》中似乎获益颇丰。尽管这组诗具有丰富的细节和精确的地貌,但它却奇怪地显示出一种普世的、近乎不带个人色彩的品质,而它讨论的却是情感范畴的极致。“目不转睛地直面糟糕”与“目不转睛地直面美好”是一对绝配,两者都对中间的东西很少关注。这就像一本书在被放回书架之前被人从结尾到开头匆匆翻了一遍。
可这本书却从未被放回书架。更像一位唯理论者而非唯情论者的哈代,自然会视这组诗为一个矫正机会,以弥补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眼中的一个不足,即他诗歌的抒情性之不足。的确,《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诗抄》迥异于他先前的墓园冥思手法,那些冥思在形而上层面上十分宏伟,但在情感方面通常却相当苍白。这就解释了这组诗大胆的诗节构成,但最重要的是,这解释了这部作品为何会将视线聚焦在他婚姻生活的初始阶段上,即他与未婚妻的相遇。
从理论上讲,此类相遇能唤起正面情感的喷发,这样的事情也时常发生。但这相遇是太久之前的事情,内省和回顾的镜片常常会显得无效。于是,这镜片便不知不觉地被我们这位诗人惯用的透镜所取代,正是透过这只透镜诗人探究着他钟爱的无穷、“无处不在的意志”以及其他一切,一边探究一边目不转睛地直面糟糕。
他似乎再无其他工具,每当他必须在动人话语和激烈言辞这两者间作出选择时,他通常都会选择后者。这或许应归结于哈代先生性格或性情的某些特定层面,但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应该还是诗歌职业自身。
因为诗歌对于托马斯·哈代而言首先是一种认知工具。他的书信以及他为其各种版本作品集所写的序言均充满对诗人地位的否定,那些文字所强调的往往是他的诗歌对他而言的日记和注释作用。我认为这些话可以当真。但我们也应该牢记,此人是一位自学成才者,而自学成才者总是对其研习对象的实质而非具体材料更感兴趣。如果他研习的是诗歌,他便会注重诗歌的启示性内涵,并往往以牺牲和谐作为代价。
当然,为把握和谐哈代曾付出超常的努力,他的技艺时常近乎典范。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技艺。他并非和谐之天才,他的诗句很少能歌唱。他诗歌中的音乐是思想的音乐,这种音乐独一无二。托马斯·哈代诗歌的主要特征就是,其形式因素,如韵脚、格律和头韵等,全都服从于他的思想之驱动力。换句话说,其诗歌的形式因素很少能派生出这种驱动力,它们的主要任务即引入思想,不为思想的发展设置障碍。
我猜想,如果有人问他在一首诗里最看重什么,是洞察还是质感,他或许会含糊其辞,但最终仍会给出一个自学成才者的回答:是洞察。因此,人们就应该依据这一范畴来评判他的诗作,其中也包括这组诗。在这组对于疏远和依恋之极端状态的探究中,他更追求拓展人的洞察力,而非纯粹的自我表现。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位前现代派诗人无人能比。同样,就这一意义而言,他的诗作的确是这门职业自身的纯粹反映,这一职业的操作模式即理性和直觉之融合。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多少有点次序颠倒了:他会直觉地面对其作品的内容;而在面对其诗歌的形式因素时,他却过度理性了。
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范例之一即他的《月光下》(In the Moonlight),此诗写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诗抄》之后两年,但它与这组诗具有某种关联,即便不是主题方面的相近,也具有心理层面的相通。
“哦孤独的工匠,你站在那儿, 像在梦中,为何你紧盯着、紧盯着她的坟,就好像那儿没有其他的坟?“如果你憔悴的大眼如此不舍她的灵魂,借助这僵尸般寒冷的月光,你或许很快便能唤起她的亡灵!”“傻瓜,我倒宁愿看见那个鬼魂,也胜过看世上所有的活人;但是,我却没有这份福气!”“哦,她无疑是你深爱的女人,一起经历悲欢,经受旱涝,她去了,你的阳光也随之泯灭?”“不,她不是我爱过的女人,所有其他人都比她重要,她终其一生我从未关心。”
“O lonely workman, standing thereIn a dream, why do you stare and stareAt her grave, as no other grave there were?“If your great gaunt eyes so importuneHer soul by the shine of this corpsecold moon,Maybe you'll raise her phantom soon!”“Why, fool, it is what I would rather seeThan all the living folk there be;But alas, there is no such joy for me!”“Ah — she was one you loved, no doubt,Through good and evil, through rain and drought,And when she passed, all your sun went out?”“Nay:she was the woman I did not love,Whom all the others were ranked above,Whom during her life I thought nothing of.”
像哈代的许多诗一样,这首诗似乎也具有民间谣曲的回声,其中有对话,也有社会评论元素。戏仿式的浪漫主义开头以及简洁单调的三行句式——更不用说此诗的标题——在当时的诗语语境中看,均显示出了某种论争色彩。这首诗显然是一种“主题的变奏”,这在哈代本人的创作中十分常见。
社会评论的调性在谣曲中通常十分尖锐,但在这首诗里却显得有些弱化,虽说还能分辨出来。它似乎是服从此诗的心理主题的。诗人十分明智地让一位“工匠”(workman),而非那位路过此地、冷嘲热讽的城里人来道出最后一节中那沉重可怕的洞察。因为,文学中充满危机的良知感通常都是知识阶层的财产。而在这里,却由这位粗俗的、近乎庶民的“工匠”出面表达了哈代所有诗歌中最恐怖、最悲剧的道白。
尽管这里的句法相当清晰,韵律一致,心理发展也很有力,但此诗的质感却因为其三重韵而削弱了诗中的思想内容——不论是从故事线索还是从韵脚自身的品质来看(尤其是后者),这样的三重韵都毫无存在的理由。简而言之,这首诗写得很专业,却不十分出色。我们得到了此诗的矢量,而非其目标。但就人类心灵的真理而言,这一矢量也许就足够了。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在这首诗里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下对自己正是这么说的。因为,“目不转睛地直面糟糕”会让你对自己的面貌一无所知。
八
幸运的是哈代活得足够长,不致落入他的成就或他的错误所构成的陷阱。因此,我们可以集中关注他的成就,或许还可以捎带关注一下这些成就的人性内涵,如果你们不愿意,也可以不谈这些。这里就有一首诗,题为《身后》(Afterwards)。此诗大约写于一九一七年,当时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在相互倾轧,当时我们这位诗人七十七岁。
当今世在我颤抖的停留背后锁上它的后门, 当五月拍打它那翅膀似的欣喜的绿叶,精致的翅膀像新纺的丝绸,邻居们会说吗:“他这个人向来喜欢留意这些事情。”如果是在黄昏,像眼睑无声地一眨,一只身披露珠的苍鹰掠过暗影,落上一丛被风扭曲的荆棘,这凝望者也许会想:“这场景他生前一定十分熟悉。”如果我的离去是在一片飞蛾舞动的温暖夜晚,当一只刺猬偷偷钻过那片草地,有人会说:“他曾力保这些无辜生灵不受伤害,但他收效甚微,如今他已死去。”如果他们听说我终于长眠,站在门口,他们仰望布满星辰的天空,如冬日所见,那些再也见不到我的人会涌起思绪吗:“对于这些奥秘他曾独具慧眼。”有谁会说吗,当我的丧钟在暮色中敲响,一阵迎面的风中断了悠扬的钟声,直到钟声再起,就像一阵新的轰鸣:“他听不见了,但他过去很留意这些事情。”
When the Present has latched its postern behind my tremulous stay,And the May month flaps its glad green leaves like wings,Delicatefilmed as newspun silk, will the neighbours say,“He was a man who used to notice such things”?If it be in the dusk when, like an eyelid's soundless blink,The dewfallhawk comes crossing the shades to alightUpon the windwarped upland thorn, a gazer may think,“to him this must have been a familiar sight.”If I pass during some nocturnal blackness, mothy and warm,When the hedgehog travels furtively over the lawn,One may say,“He strove that such innocent creatures should come to no harm,But he could do little for them; and now he is gone.”If, when hearing that I have been stilled at last, they stand at the door,Watching the fullstarred heavens that winter seesWill this thought rise on those who will meet my face no more,“He was one who had an eye for such mysteries”?And will any say when my bell of quittance is heard in the gloomAnd a crossing breeze cuts a pause in its outrollings,Till they rise again, as they were a new bell's boom,“He hears it not now, but used to notice such things”?
这二十行六音步诗构成了英语诗歌的荣光,其一切出众之处均归功于六音步。这里有一个问题:六音步诗句在这里的出现又该归功于什么呢?答案就是:为了让这位老人能呼吸得更轻松一些。这里的六音步不是为着其史诗意味,或其同样经典的哀歌意味,而是为着其三音步长的一呼一吸的特性。在潜意识层面,这种便利可以转化为富裕的时间和开阔的空白。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六音步其实就是一个拉长的瞬间,在《身后》中,随着一个又一个单词的不断递进,托马斯·哈代把这个瞬间拉得越来越长。
这首诗的构思十分简单:诗人在思考他不可避免的离去,他描绘出一年四季的四幅微型画,其中的每一幅均可能成为他的离去之背景。这首诗的题目引人入胜,它没有一位诗人在诉诸此类前景时通常会带有的情感投入,其发展基调为忧郁的沉思,人们可以设想,这正是哈代先生的初衷。但是,这首诗在其发展过程中似乎稍稍脱离了他的控制,出现了某些计划之外的东西。换句话说,艺术战胜了技巧。
但是让我们从头开始,这里的第一个季节是春天,与它一同出现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那笨拙的、几乎在嘎吱作响的优雅:五月刚一出现,重负便随即落下。这一点在读完第一句后变得越发醒目:“当今世在我颤抖的停留背后锁上它的后门”(When the Present has latched its postern behind my tremulous stay),这一句可谓相当倨傲,而且嘎吱作响,句中几个发出绝妙嘶声的咝音汇成一股,涌向句末。“颤抖的停留”(tremulous stay)是一个绝妙的词组,人们可以设想,这能让人联想到这位年岁已高的诗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为全诗的其余部分奠定了基调。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是透过二十世纪末现代诗歌语汇的棱镜来看待这一切的。在这一棱镜中显得倨傲和陈旧的东西,在当时却未必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说到催生委婉说法,死亡在这件事上独占鳌头,在最后审判时死亡可以引用这些婉辞作为它的自我辩护。以这种委婉说法的标准来看,“当今世在我颤抖的停留背后锁上它的后门”一句仅凭一点便很出色,即它表明这位诗人更关注的是他的语汇,而非他所描绘的前景。这行诗充满安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处的重音词都是两个或三个音节的单词:非重读音节以一种附言或事后补充的意味淡化了这些单词的其余部分。
实际上,六音步,亦即时间的拉长,以及其填充,全都开始于“颤抖的停留”。但直到在完全由单音节词组成的第二行中,重音落在了“五月”(May)头上,事情才真正展开。从声音角度看,第二行的总体效果是让人感觉到哈代先生的春天比任何一个八月都更加枝繁叶茂。但从心理效果上看,人们却有这样一种感觉,即琳琅满目的修饰语溢出了诗句,甚至漫入了使用带连字符的荷马式修饰语的第三行。总的感觉(体现在将来完成时中)就是,时间放慢了脚步,被每一秒钟所延缓,因为每一个单音节的词就是说出口的或写在纸上的一秒钟。
伊沃·温特斯[24]曾这样评价托马斯·哈代:“一只最锐利的观察自然细节的眼睛。”我们当然能赞叹这只眼睛——它锐利得足以把树叶的背面比作新纺的丝绸,可这却会让我们忘记去颂扬那只耳朵。如果大声朗读这些诗句,你们便会在第二行被绊倒,会把第三行的前半段口齿不清地一带而过。你们便会意识到,诗人在这些诗行里塞进如此之多的自然细节,这本身并非目的,他是为了填充格律上的空白。
事实自然是,他两者兼顾,因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然细节:一枚树叶和诗行中空间大小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可能合适,也可能不合适。一位诗人恰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悉一枚树叶以及那些重音之价值。哈代先生给出近乎扬抑格的“精致的翅膀像新纺的丝绸”(Delicatefilmed as newspun silk)这组修饰,只是为了降低上一行诗的音节密度,而非出于他对这枚树叶和这一具体感受的依恋。他如果真的依恋它们,便会将它们置于韵脚位置,或者无论如何也会让它们步出你们所见的这片音调过渡区。
但从技术上讲,这一行半诗却体现出了我们这位诗人身上深受温特斯先生推崇的那一特征。我们这位诗人自己也意识到此处的自然细节值得炫耀,便又稍加打磨。这使得他能以口语化的句式“他这个人向来喜欢留意这些事情”(He was a man who used to notice such things)来结束这一诗节。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出色地平衡了开头一句的老套华丽,而这或许正是他一开始就渴求的东西。这句话让谁来说都可以,因此他就把它算在邻居们头上,使这行诗不再像是顾影自怜,更不像是为自己写的墓志铭。
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尽管我也无法证伪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里的头尾两句,即“当今世在我颤抖的停留背后锁上它的后门”和“他这个人向来喜欢留意这些事情”,早在《身后》构思之前很久即已独立存在。自然细节被置入这两者之间纯属偶然,为的是给出韵脚(这个韵脚并不十分醒目,因此需要修饰)。它站稳位置后,便使诗人写出了这一节,全诗其余部分的构架也由此而来。
我这么说的一个证据便是下一诗节中季节的不确定性。我猜想这是秋天,因为之后的两节诗分别描写的是夏天和冬天,而且这句里无叶的荆棘似乎凋零了。这种次序在哈代这里显得有些奇怪,因为他是一个技艺高超、深思熟虑的诗人,你们可能会想,他完全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排列四季。不过无论如何,这第二节诗写得十分优美。
一切都始于另一个由多个咝音组成的词组“像眼睑无声地一眨”(like an eyelid's soundless blink)。这又是一个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假设,但我倾向于认为,“像眼睑无声地一眨”是对彼特拉克的“人的一生短过眼睑的一眨”[25]的借用,如我们所知,《身后》的主题就是一个人的死亡。
不过,即便我们不去关注这里的第一行以及其中的出色停顿,不去关注停顿之后的“眼睑”(eyelid's)和“无声”(soundless)两词之间那两个瑟瑟作响的s以及词尾的另外两个s,我们在这里仍收获颇丰。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电影慢镜头,“一只身披露珠的苍鹰掠过暗影”(The dewfallhawk comes crossing the shades to alight)。鉴于我们的主题,我们必须注意他选用的“暗影”(shades)一词。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就能更进一步地思考这只“身披露珠的苍鹰”(dewfallhawk),尤其是“露珠”(dewfall)。我们或许会问,在眼睑的一眨和前面的“暗影”之后出现在这里的露珠有什么用呢,莫非是一滴深藏的泪水?在“落上一丛被风扭曲的荆棘”(to alight/Upon the windwarped upland thorn)一句中,我们难道听不出某种被束缚或被压抑的情感吗?
我们或许听不出来。我们或许只能听到一堆重音,至多只能在“up/warp/up”的词组中想象出风吹灌木发出的响声。在这一背景中,非人称的、无动于衷的“凝望者”(gazer)一词便是描绘旁观者的合适方式,这位旁观者不具任何人类特征,仅为一种视力。“凝望者”用在这里很合适,因为他正在观察我们这位说话者的缺席,因此后者无法对他作细节描写:可能性是无法十分精确的。那只苍鹰亦如此,它拍打着眼睑般的翅膀掠过“暗影”,同样也在穿越这片缺席。叠句式的“这场景他生前一定十分熟悉”(To him this must have been a familiar sight)最具穿透力,因为它具有双重作用:苍鹰的飞翔在这里既是真实的场面,也是死后的景象。
就整体而言,《身后》之美就在于其中的每件东西均可翻番。
我相信,接下来的一节写的是夏天,第一行中的“飞蛾舞动的温暖”(mothy and warm)这两个词所具有的可触摸感便能让你们震惊,由于它们之前还有一个大胆的停顿,这种感觉便越发强烈。不过,说到大胆还必须指出,只有一位非常健康的人方能对自己逝去那一刻的漆黑夜色作如此冷静的思索,如我们在“如果我的离去是在一片飞蛾舞动的温暖夜晚”(If I pass during some nocturnal blackness, mothy and warm)这一句中之所见。更不用说他对于停顿所持的这种更为随意的态度了。“夜晚”(nocturnal blackness)之前的“一片”可能是此句中惊恐的唯一一处表露。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片”(some)一词也是一位诗人在保持其格律时可以使用的一块现成的砖石。
不过,这一节里最成功的句子显然还是“当一只刺猬偷偷钻过那片草地”(When the hedgehog travels furtively over the lawn),而这一句中最好的词自然就是“偷偷”(furtively)。其余的一切则稍稍显得有些缺乏生气,无疑也较为平淡,因为我们这位诗人显然想用他对动物王国的同情来博得读者的好感。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主题的作用下读者已经站到诗人一边。再说,如果有人真要在这里探个究竟,那他还是可以问一问那只刺猬是否真的身陷险境。不过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人会吹毛求疵。可这位诗人自己似乎意识到了他素材不足,于是在他的六音步诗行前又加上了三个音节(“有人会说”〈One may say〉),这部分地是因为,他认为言辞的笨拙能表现出温情,部分地则是为了延长这位濒死者的时间,或曰他在人们记忆中的留存时间。
在描写冬天的第四节里,这首诗开始直面缺席。
如果他们听说我终于长眠,站在门口, 他们仰望布满星辰的天空,如冬日所见,那些再也见不到我的人会有这样的思绪吗:“对于这些奥秘他曾独具慧眼。”
首先,“终于长眠”(stilled at last)既语气委婉地暗指这位正在与他这首诗道别的作者,同时也暗指逐渐归于沉寂的前一节诗。借助这一方式,比“邻居们”(the neighbours)、“凝望者”(a gazer)和“有人”(one)为数更多的读者被引入文本,并应邀在“仰望布满星辰的天空,如冬日所见”(Watching the fullstarred heavens that winter sees)一句中扮演角色。这一行诗非同寻常,这里的自然细节惊世骇俗,实为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先兆。冬日的确能见到更多的“天空”(heavens),因为冬日里树木光秃,空气纯净。如果这天空中布满星辰,那么它——冬日——见到的星星便也更多。这一行诗是描写缺席的神来之笔,但哈代先生还想再强化一下效果,于是就有了“那些再也见不到我的人会涌起思绪吗”(Will this thought rise on those who will meet my face no more)。“涌起”(rise)一词把月亮的温度传达给了这位“终于离去”的人那或许冰冷的五官。
在这一切的背后自然隐藏着那个古老的比喻,即逝者的灵魂居住在星星上。而且,这一修辞方式具有闪闪发光的视觉效果。显而易见,当你们仰望冬日的天空,你们也就看到了托马斯·哈代。在他生前,他的眼睛所观察的正是这样的秘密。
他的眼睛也观察地面。在阅读《身后》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那些将对他作出评价的人,其所处位置随着一个又一个诗节的推进似乎在不断升高。自第一诗节中的最低处,他们渐渐攀至第五诗节中的最高处。在其他诗人处这或许是个巧合,而在哈代处却并非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人物的渐进过程,从“邻居们”到“凝视者”和“有人”,再到“他们”(they)和“会有一人”(any)。这些称谓均非确指,更不亲昵。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有谁会说吗,当我的丧钟在暮色中敲响, 一阵迎面的风中断了悠扬的钟声,直到钟声再起,就像一阵新的轰鸣时:“他听不见了,但他过去很留意这些事情。”
这里没有说明具体的季节,这就是说它描写的可能是任何时间。这也可能是任何场景,或许是乡间,田野上有一座教堂,钟声悠扬。第二、三两行中的场景描述十分动人,但却过于普通,并不足以为我们这位诗人赢得任何殊荣。“一人”在他缺席的时候在“他听不见了,但他过去很留意这些事情”(He hears it not now, but used to notice such things)一句中提及的也许是诗人描述这一幕的能力。此外,“这些事情”(such things)就是一个声音,被风儿打断,但又重新返回的声音。这曾被打断、复又响起的声音在这首自传哀歌的末尾又可被视为一个指向自我的隐喻,这并非因为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声音就是为托马斯·哈代鸣响的丧钟。
真正的原因是,这个曾被打断、复又响起的声音事实上就是一个关于诗歌的隐喻,隐喻一首诗从同一支笔下流泻而出的过程,隐喻一首诗中各个诗节的排列过程。这个隐喻也暗指《身后》这首诗本身及其漂移的重音和突然出现的停顿。就这一意义而言,道别的钟声永远不会停止,至少,为哈代先生而鸣的道别钟声不会停止。它不会停止,只要他的“邻居们”、“凝视者们”、“有人”、“他们”、“一人”以及我们一息尚存。
九
在对一位作古诗人作出非同寻常的评价之前,最好先研读一下他的所有作品;我们只读了托马斯·哈代的几首诗,应该回避这种诱惑才是。在此我只需再多说一句:古往今来,只需稍稍被人阅读、便能轻而易举步出历史的诗人只有寥寥数位,哈代便是其中之一。能使哈代步出历史的因素显然就是他诗歌的内容,因为他的诗歌读来十分有趣。他的作品适合反复阅读,因为其结构往往是抗拒愉悦的。这是他投下的整个赌注,而他赌赢了。
要想步出历史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会将你带往现在。然而,哈代的诗歌在我们这里却不是一种十分令人自在的存在。他很少被研究,更少被阅读。首先,至少从内容上讲,他便能让后世诗歌的大部分成就黯然失色;与他相比,许多现代派巨人都像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对于无生命者的强烈兴趣显得既缺乏吸引力又让人不安。这里所体现的与其说是普通公众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如说是他们的精神膳食构成。
当他步出历史、局促不安地置身于现在时,人们可能又会认为,未来或许是他更合适的去处。这很有可能,尽管我们此刻所见证的技术和人口巨变似乎会抹去我们根据自己的相关经验作出的所有预见和想象。不过这仍有可能,而且并不仅仅因为那战无不胜的“无处不在的意志”在其荣光的顶峰会突然决定感谢其早先的卫士。
这很有可能,因为托马斯·哈代的诗歌向一切认知的目标——无生命事物——大大推进了一步。我们人类早已开始这一探求,我们不无根据地假设,我们的细胞结构与无生命者相似,如果存在着一个关于世界的真理,这个真理一定是非人类的。哈代并非一个例外。他身上例外的一点就是他的寻求之执着,在这一寻求过程中,他的诗歌在主题方面,尤其是音调方面开始获得某种非人类的特征。这自然可被视为一种伪装,一件战壕里穿的迷彩服。
或是本世纪英语诗歌中流行的一种新时装:不带感情色彩的姿态实际上成为了惯例,冷漠的态度成为一种手法。不过这些都是副产品。我猜想,哈代先生之所以探究无生命的事物,并非为了扼住它们的喉咙,因为它们没有喉咙,而是为了获得它们的语汇。
细想一下,“就事论事”这个说法可以很好地概括他的语言风格,只不过重音应该放在“事”上。他的诗歌发出的声音,往往就像事物获得了话语的力量,这也是其假扮人类的另一层伪装。在托马斯·哈代这里,情形或许正是如此。但话说回来,这件事也不足为奇,因为有个人(此人更像是我本人)曾说,语言就是无生命者向有生命者道出的关于其自身的第一行信息。或者更确切地说,语言就是物的稀释形态。
或许正因为他的诗歌几乎始终如一地(只要诗行数超过十六行)或者显露出无生命者的气息,或者时刻关注着它的面庞,未来也许会为他辟出一个比他现今置身的场所更大的空间。我们可以如此转述《身后》一诗:哈代习惯于关注非人的物,他那只“关注自然细节的眼睛”即由此而来,那大量关于墓碑的沉思亦源于此。未来能否比如今更好地理解统领万物的法则,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看来它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人类和无生命者之间存在更大程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程度超出了哲学思想和文学的一贯估计。
正是这一点可以让人们在水晶球里看到许多陌生的东西,它们身着奇装异服,在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26]出版的《哈代作品集》或“企鹅版”的《哈代作品选》中来回奔跑。
[1] 1994年秋在蒙特霍利约特学院(又译霍山学院或曼荷莲学院)为选修“现代抒情诗主题”课程的学生所作的演讲。——原注。译者按:此文原题“Wooing the Inanimate. Four Poems by Thomas Hardy”,俄文版题为“С любовью к неодушевленному. Четыр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Томаса Гарди”。
[2] 指英国批评家、诗人艾尔瓦列兹(1929年生)为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希尼(1939—2013)的诗集《农活》(1979)所写书评,载《纽约图书评论》1980年3月6日。
[3] 拉福格(1860—1887),法国诗人,被视为象征派诗歌的先驱之一。
[4] 此处比较有其出处:艾略特在《荒原》第一部《逝者的葬礼》中有“我要用一把尘土来向你展示恐惧”(I will show you fear in a handful of dust.)一句,而哈代在《雪莱的云雀》中则有“促使诗人作出预言的,/仅为一小撮无形无备的尘土”(That moved a poet to prophecies —/ A pinch of unseen, unguarded dust.)一句。
[5] 此诗写于1914年,题为《自然就是罗马》。此诗直接自俄语译出。
[6] 即但丁·罗塞蒂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7] 以上诸君均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人。
[8] 《约翰福音》的第一句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9] 英国乔治诗派出现在20世纪初,因该派诗人编辑的《乔治诗集》(Georgian Poetry)得名。
[10] 这里的“世纪之末”用的是法语“findesiècle”。
[11] 此处的“死神舞蹈”用的是法语“danse macabre”。
[12] 这两个词组分别出自奥登的诗作《西班牙》和《阿喀琉斯的盾牌》。
[13] 叶芝的《第二次降临》一诗中写到鹰,其开头两句即为:“在不断扩大的涡流中转圈,/雄鹰听不见放鹰的人。”
[14] 叶芝《第二次降临》的结尾两句是:“哪只粗暴的野兽终于等到时辰,/要慵懒地前往伯利恒投生?”
[15] 邓巴(约1460—约1520),苏格兰诗人。
[16] 火蜥蜴的形象和这个词本身(Salamander)都来源于蝾螈,中世纪的炼金术士认为它是统治火元素的精灵,同时Salamander还用来指冶炼炉中的通条。
[17] 康拉德(1857—1924),波兰裔英国作家,这里指的可能是康拉德的小说《机会》(1913)。
[18] 美国第四十任总统是里根。
[19]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为罗密欧和朱丽叶秘密证婚的神甫。
[20] Jar一词同时又有“罐子”之意。
[21] 作者在这个单词中用斜体标出的前半部本身又有“电影”之意,但这层意思的产生年代晚于1912年。
[22] “不祥之兆”的英文原文为the writing upon the wall,字面意义为“墙上的文字”。
[23] 典出《圣经·旧约》之《但以理书》第5章:伯沙撒王设宴款待宾客时突见一只手在粉墙上写下文字,大臣智士竟无人能识,仅但以理能解:“弥尼”即上帝,这几个字的意思即:“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与米底亚人和波斯人。”
[24] 温斯特(1900—1968),美国诗人、批评家。
[25] 语出彼特拉克的《悼萝拉》。
[26] 1846年创建于纽约的一家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