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阅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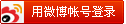
x
文/马永波
摘 要:马克•斯特兰德善于把自我对象化,对自我及其所置身的世界进行有距离的观照,这种旁观者视角使得他的观察获得了某种“公正性”和“客观化”,从而打破自我和私人化,成为事件和风景的编年史见证人。主体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形而上学的“自我”,而是陷入了悖论式循环的“递归的自我”。这种自我在场的取消,不但使主体性陷入了机械学的递归循环,也使语言陷入了类似的指涉循环。在这种状态中,自我和语言不再是指涉的和表现的,而是表演的和自我同一的。这种“最终的自我取消”绝不意味着对死亡的形而上诉求,而是重新寻回万物一体的本质同一性,以克服西方文明中主客观二元对立思维所造成的种种分裂与现代性危机。

马克•斯特兰德引起我的注意还是在我翻译他所编辑的《当代美国诗人:1940 年后的美国诗歌》时,作为成就卓著的名诗人,他在那本选集里只谦逊地选了自己的一首短诗《保持事物完整》。在很多诗人为诗歌读者越来越少的困境所惑时,他在一次访谈中的回答顿时令这个问题成为了伪问题——“诗歌的读者实际上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是不断变换的。很多人一段时间对诗歌感兴趣,而后落在后面,失去兴趣,又对另外的事情发生兴趣。但新的人永远在加入。读者少干扰不了我。我不相信诗歌是为每一个人的,正如我相信炖猪肉是为每一个人的。诗歌是有要求的。它要求花一段时间习惯,一段‘入门’时期。只有那些愿意下功夫于此的人才能从诗歌中真正受益。不,缺少读者干扰不了我。一些诗人有十万名读者,但我不相信那么多人能真正读懂诗歌。如果我有那么多读者,我就会开始觉得我的诗哪儿出了问题了。”[1]539以读者体重总和为判断艺术标准的时代永远过去了。斯特兰德本身是个让人仰望的诗人,可是他也有自己的英雄,这里边包括詹姆斯•梅里尔(“没人有那样的技巧”)和已故的约瑟夫•布罗茨基。有那么几年,斯特兰德每年都给布罗茨基寄新年贺卡。“我从来不知道是否他收到过我的贺卡,因为他从来不回复。后来他来美国时我见到了他。我介绍说自己就是写那些贺卡的作者,让我吃惊的是,他一行接一行地背诵出了我寄给过他的一首诗。我跪了下来,吻了他的裤腿。”
斯特兰德属于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国新诗人。他通常被归为新超现实主义阵营,该阵营还有詹姆斯•迪基、默温、高尔韦•金内尔、唐纳德•霍尔、查尔斯•西密克、约翰•海恩斯等诗人。这个流派普遍受到西班牙和拉美超现实主义的影响,竭力摆脱思想意识的控制,深入挖掘潜意识领域,富有梦幻色彩。而梦幻作为清醒和睡眠的中介,既不受理性机制的审查,又可以感知梦的全部过程,记录下意识与无意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流与对照,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使精神的隐喻活动得到解放。斯特兰德的诗在抽象和经验的感觉细节之间取得了平衡。他的声音在平凡和崇高之间轻松地移动,创造出一个视觉清晰度极高的空间,这得宜于他早年对绘画的兴趣和大学后对美术的专门研究。他的诗中充满了“离别的气氛”,同时也具有出人意料的幽默。自我的消除和时间的剥夺被视为悲哀的来由,但也是庆典的基础。他的诗歌以机智和坚忍克制使这个艰难的真理戏剧化了。斯特兰德善于超过自我的界限,把自我对象化,对自我及其所置身的世界进行有距离的观照。这种从远离自我的视角所进行的观察带来了旁观者的观点、幽灵的语气,一切都朦胧神秘,似幻似真。他把聂鲁达的梦幻性质与梦魇结合起来,让人想起特拉克尔这样的欧洲表现主义者。如他的语言清晰而单纯,具有深沉的内向性,多诉诸日常生活的意象。
斯特兰德的诗中弥漫着一种个体在广阔的异化世界中无能为力的感觉,某种程度上和卡夫卡非常相像,他被称为“最深的异化的哀悼者”。他曾在一篇访谈中谈到:“世界是势不可挡的,而人是很弱小的。一个人甚至没有力量去对付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 [1] 541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抛弃自我本性、远离最具创造性的源泉的过程,世界以命令的方式支配着我们,教导我们不要想像和幻想,要做一个顺从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提前死亡。《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一诗展现了诗中人在周围成年人(世界)的怂恿下,再次杀死自我的过程。
在诗里,诗人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这种意识的双重性允许诗人从自我的远处产生最大清晰度的观察,从而取得摄影的客观化效果,更凸显了异化的残酷。《邮差》、《地道》等诗都表现了这种发现:自我是他人,甚至是他物。迫害者是自我,受害者是他人。而他人也是自我。这种万物同源的整体自我观给斯特兰德的诗蒙上了神秘、悲哀而又欢愉的色彩,实现了最终的自我取消。自我是异化最深的源头。“他人就是地狱”(萨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不可通约性已经达到了除了利益关系,人际之间再难发生任何其他关系。只要有他者在场,自我的异化就是必然的,他者具有将自我僵化为对象和客体的作用,类似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目光。当自为的存在变为为他的存在时,异化便成为可能。沉沦在此中与他人共在的人已失去本真的存在,同他人相处,就是想把他人当做客体和对象,而竭力摆脱自己被他人目光对象化的地位,在他者的注视下,纯粹主体将不复存在。海德格尔把人的相互共在描述为:“互相反对、互不相照、望望然去之、彼此无涉……上述最后几种残缺而淡漠的模式能说明日常的普通的相互共在之特点。”常人求异,领悟者求同。斯特兰德所主张的“最终的自我取消”绝不意味着对死亡的形而上诉求,而是重新寻回万物一体的本质同一性。他将自我分裂以实现对自我的观察与审视,最后将自我等同于他者,这种立场和身份的转换,使他的诗歌获得了某种观察的“公正性”和“客观化”。打破自我和私人化,就是背叛“最小化借口”,从而成为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事件和风景的编年史见证人,从“最小化”达到关注普遍的“最大化”。他利用个人性达到非个人性。他诗歌中的“我”既不是一个“角色”(persona),即一个为全体代言的“我”,也不完全是自白性质的。当自我分裂而形成的二元自我(甚至不断互相超越的多元自我)在梦魇的情境中重新合而为一,实际上就已经导致了自我的最终取消。自我是他人、他物,而他人无一是他人本身。在这种连锁反应中自我将永远无法凝成孤立的定在,在游移和变幻中循环无定。这种自我取消的声音帮助诗人对当代世界中个体的构成和定义进行个人化的探索,在这样的世界中,“被抛入”的个体感觉不到真实的关联和角色,除了成为一个空虚的填充物。正如他在《保持事物完整》中说到的:“在田野中/我是田野的/空白。/这是/经常的情况。/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是那缺少的东西。//当我行走/我分开空气/而空气总是/移进/填满我的身体/曾在的空间//我们都有理由/移动。/我移动/是为了保持事物完整。”[2]对于自在的宇宙而言,人是多余的。自我的真正工作就是放弃:放弃地点,放弃同伴,放弃所有可辨别的物理标记,除了美本身。这种放弃从来没有受到个性的妨碍。这种极端的放弃也不能混同于谦逊或者禁欲主义。在对自我多重性的既深入又超离的过程中,诗人获得了他所称道的“有同情心的距离”(compassionate distance)。诗歌中作为说话者的个人的“我”又无意中抵消了主题向公正和客观发展的有意趋向,因此,我们常常能在他的诗歌中发现这种辨证的胶着处境,那种用朴实的语言实现的自我与虚无之间的调停——“到这里来/有奖赏:没有什么许诺,没有什么被带走。/我们没有心或者救赎的恩典,/没地方可去,没理由留下。”(《到这里来》)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本来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同一性,在看似毫无关联或者截然相反的事物背后存在着普遍相应关系和真实本质,只不过由于语言对事物的命名(文明化)而使事物脱离了这种整体的同一。因此,生与死、高与低、过去与未来、想像与现实、政治与艺术、主观与客观,都是一个普遍问题的特殊形式,这个普遍问题就是人的生存状况。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去,这些二元对立的矛盾将趋于消弭。
斯特兰德所接受的影响很多,其中包括巴西诗人安德拉德、华莱士•斯蒂文斯,当然,还有博尔赫斯。他的风格奇妙地混和了心理越轨和梦魇状态,不时地以坚忍克制、疏远的放弃介入其中。
凝视虚无就是用心灵来熟悉
我们都将被卷入的一切,将自己暴露给风
就是感觉附近某个不可把握的地方。
(《夜,门廊》)
虽然斯特兰德也写短篇小说,他还是以诗歌最为著称,而博尔赫斯对他的影响在他最早的选集里表现得最为鲜明。其中斯特兰德面临着他的自我是他者的梦魇的含义,他经常描写一个梦一般的、有时是博尔赫斯式复合物组成的循环世界,那里,“最糟糕的一直在等待/围绕着下一个角落或者隐藏在干燥/摇晃的病树的枝条中,犹豫着/是否要掉落到行人身上。”斯特兰德后期的作品,最著名的是《我们的生活故事》和《未讲的故事》,其突出标志是一种自我指涉性,这和博尔赫斯短篇小说伪装成的论文不无相似之处,它们经常遵循一种递归或循环的思想模式,类似于《巴别图书馆》的结构。但是博尔赫斯对他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影响可以在斯特兰德早期的杰作《镜中人》中见出。镜子是博尔赫斯最喜欢的一个主题,它兼具他性、自恋、冥想的传统和原型涵义。在他的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比奥依•卡萨雷斯说,“镜子和男女交媾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3]73类似地,在斯特兰德的诗中,说话者的自我在镜子的反射中加倍了,成了一个第二自我,“一个巨大的绿月亮/一处光遮盖着的青肿。”和博尔赫斯另两个小说《博尔赫斯和我》及《1983 年 8 月 25 日》类似,说话者自言自语地说:
你在那里。
你的脸是白的,扳着,肿了。
你头发坠落的尸体
沉闷而不相称。
埋在你口袋的黑暗里,
你的双手静止。
你几乎没有醒过来。
你的皮肤沉睡着
而你的眼睛躺在
眼窝的深蓝中,
无法够到……
试比较博尔赫斯的小说《1983 年 8 月 25 日》:
在无情的灯光下,我与自己面对面地相遇了。在那张狭小的铁床边,背朝我坐着的正是我,显得更加衰老、瘦削和苍白,眼睛注视着房间高处的石膏装饰线条。而后我听到一个声音。那不完全是我的声音;而是我经常在我的录音机中听到的那种不快的、没有音调变化的声音。“真怪,”那声音说。“我们是两个人,又是同一个人。但是在梦中这就没什么奇怪的了。”[3]473
曾经有人问斯特兰德,博尔赫斯是不是对他影响最深的诗人,斯特兰德回答:“哦,是的,但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小说。博尔赫斯是个如此神奇的作家,尤其在某些事情上。我特别喜欢他的《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
这种复数写作法与兰波的“我是另外一个人”、雅克•拉康的“无意识是另一个人在讲话”如出一辙。这样的自我是被社会拒绝的喑哑的受害者,是被消过毒的。他平静而绝望地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异化的故事——某个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家草坪上的人怎样弄得他心烦意乱;无法忍受的他只好朝邻居家的院子挖了一条地道,“从一所房子的前面出来/站在那里,疲倦得/不能动弹,甚至说不出话,希望/有什么人会来帮助我。/我感觉自己正在被观察着/有时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但什么都没有做/而我已经等待了多日。”(《地道》)
在荷兰“图形艺术家”埃舍尔的木版画和平版画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类似于诗歌之中的这种自我复制和循环。埃舍尔表现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自我复制,平版画《互绘的双手》就表现了这个思想——双手互绘对方,互绘的方式就是意识思考和建构自己的方式,在这里,自我和自我复制是连结在一起的,也是相互同等的。自我复制还具有更大的功能——世界万物的构成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自我复制。从信息理论角度说,我们人类的确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以 DNA 的形式携带了我们个体的完整信息,“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4]在更深层次上,自我复制是我们的认知世界互相反映和互相交错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本书里的正在读他(或她)自己的故事的人物,或者像反映它自身风景的一面镜子。不同世界的相互交错取消了彼此间的差异,使得事物完全可以既是其本身又同时是其他某物,甚至任何物(anything and everything)。因而,虚幻和现实、原因和结果可以互为表里、互相混淆。内与外的形而上学对立的虚构性质可以用著名的“莫比乌斯带”(Mbius strip)来说明,这个概念是由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Augustus Mbius,1790—1868)首先创造的。莫比乌斯带很容易制作,只要将纸条扭曲 180 度,用胶水或胶带粘住两头,就成了一个只有一个面和只有一条边的曲面。这个令人感兴趣的性质使你能够设想一只蚂蚁开始沿着莫比乌斯带爬,那么它能够爬遍整条带子而无须跨越带的边缘,你将发现它不是在相反的面上爬,而是都爬在一个面上。要证实这一点,只要拿一支铅笔,笔不离纸地连续画线。空间位置的这种变换使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外相通,分不出哪是里面,哪是外面,哪是正面,哪是反面。由此也演变出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1882 年,著名数学家菲立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瓶子”。这是一个像球面那样封闭的(也就是说没有边)曲面,但是它却只有一个面。我们可以说一个球有两个面——外面和内面。如果一只蚂蚁在球的外表面上爬行,那么如果它不在球面上咬一个洞,就无法爬到内表面上去。但是克莱因瓶却不同,我们很容易想像,一只爬在“瓶外”的蚂蚁,可以轻松地通过瓶颈而爬到“瓶内”去——事实上克莱因瓶并无内外之分!
数学家哥德尔于 1931 年提出了激进的“不完全性定理”——任何封闭系统中都包含在系统自身内部不可证明的命题。这个定理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陈述是假的”这样的递归悖论能够在一个语言系统内存在,却不能在该系统内部得到满意的理解。理解这样的陈述需要跳到语言系统外部一个更高的“元”层面上去。递归网络和元数学的思维方式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打开了大门。
在斯特兰德的诗歌中,主观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形而上学的“自我”,而是陷入了悖论式“奇异循环”,重新被概念化了。“自我”现在是一个机械学结构的副产品,其中一个想像着的头脑在想像自己在想像自己,如此永无止境。斯蒂文斯的晚期诗歌中也多有表现,他用“最高虚构”来称谓一种不可抵达的、理想化的“元”诗学。“递归的自我”取消了自我的在场,不但主体性陷入了机械学的递归循环,语言也类似地陷入了指涉循环。为了超越这些怪圈,也许我们可以诉诸音乐的状态,将语言的下限和音乐的上限整合起来。在这种状态中,自我和语言不再是指涉的和表现的(referential and expressive),而是表演的和自我同一的(performative and self-identical)。
在马克•斯特兰德谜一般的《我们的生活故事》中,诗人以诗歌的形式演示了这种类似埃舍尔“自噬蛇”(self-engulfing snake)绘画的奇异的递归结构(Recursive Structures)和超穷推理。它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思想,我们不仅在阅读或者检查我们的生活故事,我们也在书写我们的生活故事。我们同时是生活戏剧的演员和观众。仅仅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是不够的。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我们也必须把我们自己写入存在中。“书”,“我们生活的故事”,似乎拥有自己的生命,决定着叙述者的所为和所写。而且,书似乎是自我限制的,几乎像是已经预先决定了叙述者的生活,因为书“精确得”令人恐惧。但是,作者想从“书”中走出来,也许是走出过去,他似乎无法做到这点。过去束缚着我们,就像它使我们成为可能一样。诗中人试图相信生活要多过写在书中的东西,但是当他们关于生活是否更多意见不一致时,他们发现他们意见不一致的部分被写在了书里:
这个早晨我醒来,相信
我们的生活并不多过
我们生活的故事。
当你不同意时,我指出
你不同意的部分在书中的位置。
你倒头睡去,我开始阅读
当它们被写下时
你曾经加以猜测的神秘的部分
它们在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后
就变得兴趣索然了。
在我们参与事件之前,它们往往显得很有吸引力,甚至是“神秘的”,可一旦我们经历过了,它们就变得沉闷和平凡,变得兴趣索然,尽管它们依然是我们的一部分。只有从一定的距离之外去看时,只有在半遗忘之中,“书”才重新变得有趣。显然,因为我们遗忘了做一个孩子是怎么回事,重新温习书的那一部分就再次变得有趣了。我们大多数人带到自己成年生活中的愤世嫉俗消逝了。从一个距离外看去,童年似乎是一段无忧无虑的乐观的时光。
做梦,和回顾我们的童年一样,是另一种超越“书”的方式,至少是对它的逃避。做梦是重新控制你的生活的一次尝试,是对“你的生活故事”的超越,是变得比你过去的总和更多。它甚至无需是字面意义上的做梦;个人的渴望,“一个故事的不成功的形式”也可能是成为比你本身更多的一种方式。当我们翻动过去的书页,它们照亮了我们所想的一切和我们即将相信的一切:
每翻动一页就像一根蜡烛
在头脑中移动。
每个瞬间就像一次无希望的原因。
我们要是能停止阅读就好了。
他永远不会想读另一本书
不幸的是,仅仅是注视着过去并不总是能鼓舞我们;事实上,它恰恰造成了一种绝望感。是未来,是对更好的事物即将到来的希望最容易鼓舞我们。
书的错误之一是它仅仅揭示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书从来不讨论爱的原因。
它声称混乱是一种必要的善。
它从来不解释。它只是揭示。
过去事件的记录仅仅揭示了所发生的事情;它没有解释它们发生的原因。凭借事件本身甚至不能真正地揭示我们是谁。当然,了解发生的一切是通向自我发现的第一步。
随着诗的展开,逐渐变得明显的是,诗中的男人和女人已经慢慢地不爱对方了。尽管是词语引起了两人之间的分裂,只有更多的词语,那从未说出过的词语,能够弥合他们之间存在的裂缝。因为他们还没有从对方那里听到将克服他们之间差异的词语,他们必须“秘密地拼凑起他们的生活”。回顾过去无济于事,除非人们愿意因为回顾过去而做点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诗中人似乎比书中人还不真实:
他们在沙发上并排坐着。
他们是从前的自己的
副本,是厌倦的幽灵。
他们的姿势是厌倦的。
他们凝视着书
为他们的无知,
以及不情愿放弃而惊恐。
他们在沙发上并排坐着。
他们命定要接受真相。
任何真相他们都会接受。
书必须要写
必须要读。
他们就是这书,此外
他们什么都不是。
诗中人不再真正地活着;他们让自己成了他们曾经之所是的纯粹的影子,被他们早先的“纯真”而“惊恐”,准备放弃,准备“接受真相”。如果他们曾经不愿接受失败,他们现在则接受了他们仅仅是自己的过去、再无更多这样的思想。
作为新超现实主义的一员,马克•斯特兰德在深刻表现了现代社会中普遍的异化危机之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显示出拒绝异化的勇气,他没有走向虚无,而是利用语言和虚无进行了一场无休止的对话。自我的消除既是他哀悼的理由,也是他庆祝新生命诞生的开始,因此,他的自我的挽歌始终在忧郁压抑的背景中透出一抹欢快的亮色。正如帕斯所言,“马克•斯特兰德选择了否定的道路,他把丧失作为通向完满的第一步。”这种否定其实是真正的肯定,因为它见证了放弃的力量——要得到生命,必先放弃生命。
参考文献
[1] 王家新,等. 二十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2] 马克•斯特兰德. 当代美国诗人:1940 年后的美国诗歌[M]. 马永波,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37.
[3]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 王永年,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4] 大卫•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3.
作者简介:马永波(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文艺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现代诗学、比较文学、西方文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