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阅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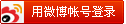
x
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出生于瓦尔特河畔的琅茨贝尔格,在布隆贝尔格和柏林长大,在慕尼黑、日内瓦、巴黎和柏林读了哲学、罗马语文学和日耳曼学专业。1920—1935年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罗曼语文学教授,1935年因其犹太出身被解聘。1945年后恢复了德累斯顿教职。此后在格莱弗斯瓦尔德、哈勒以及柏林任教授。克莱普勒给自己最“艰难”的作品命名为《第三帝国的语言》,它令这位学贯罗曼学、日耳曼学和比较文学的作家声名远播,跨越了欧洲大陆。不仅因其是第一本对“第三帝国语言”的深刻评析,也不仅因作者所表现出的语言天赋,更因为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人道主义的文献。
第三帝国的语言 ——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节选)
曾经有过BDM、HJ和DAF以及无数的其他类似的缩略符号。
在我的日记本里,LTI(第三帝国的语言)这个符号最初是个语言游戏,带有模仿戏谑的意味,然后很快就成为一种仓促的记忆的紧急救助了,作为在手帕上系的一种结扣。没过多久,它又成为那全部苦难岁月里的一种正当防卫,成为一种向我自己发出的SOS呼叫。一个很有学问的标记,就像第三帝国不时地喜欢响亮的外来词语一样:“确保”(Garant)听起来比“担保”(Bürge)更重要,而“诋毁”(diffamieren)比“搞坏名声”(schlechtmachen)更有力。(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懂它们,但正是对于不懂的人来说,其作用才更为显著。)
LTI:Lingua Tertii Imperii,第三帝国的语言。我那时老是会想到一则老柏林人轶事,那应该是出自我那本格拉斯布莱诺的漂亮绘本,那位三月革命的幽默大师的作品——然而,我的藏书到哪里去了,我到哪儿去查阅它?到盖世太保那儿寻问我的藏书有意义吗?……“爸爸”,一个小男孩在看马戏表演时问道,“绳索上的那个人拿着杆子在干什么呢?”——“傻孩子,那是根平衡杆,他靠它稳住自己。”——“哦,爸爸,如果他把它弄掉了怎么办呢?”“傻孩子,他紧紧地抓着它呢!” 我的日记在这些年里一直是我的平衡杆,没有它我早已经摔下去上百次了。在感到恶心和渺无希望的时候,在机械的工厂劳动无尽的荒凉中,在病人和死去者的床边,在一个个墓碑旁,在自己内心的困窘中,在极端耻辱的时刻,当心脏在物理意义上停止工作时——总有这个自我要求来帮助我观察、研究、记住正在发生着什么——明天它就会是另一副样子,明天你对它的感觉就会不同;记下它现在的样子和表现。然后很快,这一呼唤就会密集起来,它要我将自己凌驾在那个境遇之上,维护内心的自由,进入那个始终发挥着效用的秘密公式:LTI,LTI!
即便我有意,要发表这个时期全部的、记录了所有日常经历的日记,我仍然会以这个标记作为它的书名,不过我并没有这种打算。人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比喻。因为正如常常会有“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面目”这样的说法一样,一个时期的表达同样被视为这个时期的语言。第三帝国的语言带有一种十分可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出自它所有的生存表述和遗物:出自它豪华建筑无度的夸耀及其废墟,出自它的战士类型,那些被他们作为理想的形象定格在总是不同的、又总是相同的广告牌上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士兵,出自它的高速公路和群葬合墓。这些都是第三帝国的语言,这一切当然都会在这本书稿中谈到。只是,当一个人从事一种职业已经几十年,而且是非常喜爱地从事它的,那么这个职业最后必然会给他留下深深的烙印,甚于其他任何东西的影响,所以,这确确实实是语文学原本意义上的第三帝国的语言,是我紧紧抓牢的东西,是我的平衡杆,它帮助我度过了荒凉的十小时工厂劳动,挺过了抄家、逮捕、虐待等等等等带来的恐惧。
人们总是不断地引述塔列朗(Talleyrand)的句子,说语言是用来掩饰外交官的(或者干脆说某个狡猾的和值得怀疑的人的)思想的。然而正确的说法应该正好相反。不管在别人面前还是在自己面前,一个人故意要掩饰的东西,包括他不自觉隐藏于内心的东西:其语言会令之昭示于天下。这应该也是这句话的含义:le style c’est l’hommele;一个人说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谎言——但是在其语言风格中,他的本质会暴露无遗。
这个原本意义(语文学的“原本意义”)上的第三帝国的语言在我的感觉中是很特别的。
希特勒青年团
刚开始的时候,当我还没怎么遭遇到、或者只遭遇到很轻微的迫害时,我厌烦橱窗的语言,广告牌的、棕黄色军装的、旗帜的语言,向希特勒致敬伸直的手臂的、修剪整齐的希特勒胡须的语言。我逃避,埋头沉潜进自己的职业,我讲着我的课,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面对着眼前越来越空荡的课桌椅,仿佛视而不见。我全神贯注地写作我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普遍的状况已经够让人窝火的了,为什么还要让纳粹的文字来进一步破坏我的生活?假使我偶然或者是因为误会拿到了一本纳粹的书,读了第一段我就会把它扔到一边去。街上若有什么地方响起领袖的或者是他的宣传部长的声嘶力竭的怪叫,我总要绕一个大圈子避开高音喇叭;而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我总是揣测不安地尽力将赤裸裸的事实——它们的赤裸裸表现已经令人心寒无比——从那些讲话、评论和文章的令人作呕的浑汤中打捞出来。而当公务员遭遇清洗,我就直接想办法把自己与现实隔绝开来了。那些如此落伍的、早已被每一个顾惜自己的羽毛、在意自己形象和身份的人加以诋毁的启蒙者,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一直是我的最爱。现在,我可以把我的全部时间和工作精力都转向我已有长足进展的学术作品;要说涉及十八世纪的资料,我坐在德累斯顿的日本宫里,就如同“身居肥油里的蛆虫”;任何一家德国的图书馆,甚至巴黎国家图书馆,都不可能给我提供更好的养料了。
但是很快,使用图书馆的禁令降临到我头上,于是我手中的生命之作被剥夺。接着是我被扫地出户,再接着就是一切随之而来的东西,每天一个新的随之而来的东西。这时,平衡杆便成了我最须臾不可离弃的器械,时代的语言成了我最大的、第一位的兴趣所在。
我越来越仔细地观察,工人们在工厂里是怎样说话的,盖世太保畜生们怎么说话,在我们这儿,在犹太人牢笼的动物园,人们怎样说话。我察觉不到很大的区别;不,其实完全没有区别。所有的人,追随者和反对者,既得利益者和牺牲者,都毫无疑问地接受同样的样板引导。
我试图寻获这些样板,这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无比简单的,因为在德国印刷和谈论的所有东西,完全都是从统一模子里出来的;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偏离这一种被允许的形式,都不可能跻身进入公众视野;书籍、报纸、给政府部门的信件和服务行业的表格——所有东西都在同一个棕色的汤汁里漂浮,而书面语言的这种绝对的统一性也解释了演讲形式的同一性问题。
然而,如果说寻找样板这样的事,对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来说不过形同儿戏的话,对我来说则艰难无比,而且总有风险,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可能。购买、包括借阅任何种类的书籍、杂志和报纸,都是佩戴黄星标志的人所不允许的。偷偷收在家里的书报意味着危险,它们被藏在橱柜和地毯下面,炉顶和窗帘架上面,或者作为点火材料储存在煤堆边上。当然,类似的做法只有在运气好的情况下才行得通。
从来没有哪一本书,我这一生都没有,像罗森贝尔格(Rosenberg)的神话书那样,令我的头脑如此震动。并不是因为他意味着一种特别深刻的、难以理解的或者震撼心灵的阅读,而是因为克莱门斯拿着这本书往我头上足足夯了好几分钟。(克莱门斯和魏瑟是德累斯顿专门折磨拷打犹太人的家奴。人们一般分别称他们为打手和啐嘴。)”反了,你这个犹太猪竟敢读这样一本书?”克莱门斯吼道。在他眼中,这简直是一种对贡品的亵渎。“你怎么胆敢把图书馆的书拿到这儿来?”我之所以得以解脱,没有被送进集中营,是因为可以证明这本书是在雅利安妻子的名下借出来的,而且关于这本书的笔记被撕得粉碎,完全无法辨认。
所有的资料都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弄来,被悄声无息地吸纳汲取。而同时又有多少资料我根本无从获取!因为,每当我为一个问题试图深入源头、寻根究底的时候,当我,简单地说,需要专业知识方面的工作资料的时候,那些小图书借阅室就对我失去了意义,而公共图书馆则将我拒之门外。
有些人可能会想,专业上的同事们或者那些年龄较大的、在此期间有了公职的学生,应该是能够帮助我克服这种困境的,他们应该可以作为中转者,帮助我借阅书籍。唉,亲爱的上帝!那可是要求个人勇气、承担个人风险的一种行为。我曾经常常在讲台上引述一句漂亮的法语古诗。一位落难的诗人伤痛地回想众多的amis que vent emporte,et il ventait devant ma prote,“被风刮走的朋友,那时我的门前风正急骤。”不过,我必须公正地说,我也找到了忠实勇敢的朋友,只是,这中间正好没有关系密切的专业同事或者职业相近的人。
所以,在我的笔记和摘要里总留有类似这样的注脚:以后确认!……以后补充!……以后回答!……而后来,当经历这个以后的希望越来越小时,我改写道:这里以后还需要加以充实……
而在今天,当这个“以后”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但是马上就会变成现实的时候,因为书籍从瓦砾和交通的困境中重新浮现出来(同时,因为可以问心无愧地从共同建设者的Vita activa 中重返书斋),而我今天却知道,我将不会有这个能力,将我关于第三帝国的语言的观察,我的反思和问题,从勾勒描述的状态提升到一个完整的科学著作的形态了。
做这件事情需要更多的知识,并且也应该需要更多的生存时间,这不是我,也不是(目前情况下)任何一个个人所拥有的。因为这里需要完成非常多的极为不同的专业劳动,日耳曼语学者和罗马语族语文学者,英语语言学者和斯拉夫语语言学者,历史学者,民族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和神学学者,技术工作者和科学家们,他们得首先进行很多的相关研究,通过一系列博士论文解决很多的个别问题,然后才可能有一个勇敢的和无所不包的头脑来进行大胆的尝试,全方位地把这个 Lingua Tertii Imperi表现出来,这个全方位涵盖了它最贫困不堪的和最富有丰盛的一面。不过,一个最初的尝试和探寻,探查那些依然流动不定的事物,这种法国人称之为第一时间的工作,对于未来真正的研究者们总是有其价值的,而且我相信,这些以半成品状态呈现的研究对象,它们一半是具体的经历讲述,一半已经进入到形而上的科学观察阶段。
然而,如果这就是我的出书意图,那我为什么不让这本语文学者的记录,直接从那本艰难年代留下的、更加私人也更加一般性的日记里剥离出来,交付出版?为什么还要从整体的角度对这一点和那一点进行概括?为什么还如此频繁地把今天的、希特勒后第一时间的观点与当时的观点放在一起呢?
我将细致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中有一种倾向,因为我在寻求科学之用的同时,还怀有教育之图。
目前,人们老挂在嘴边的话题是清除法西斯主义的观念,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战犯们被绳之以法,“小党员同志”(kleine PG.s)(第四帝国的语言!)被开除了公职,纳粹书籍也从公共视野中消失,那些希特勒广场和戈林大街都改了名,希特勒橡树也被砍了。但是第三帝国的语言似乎仍然要在一些富有特征的表述里保持下去;它们渗透之深,似乎将在德语语言中占有一席永久之地。比如说,1945年5月以来,我在多少次广播讲话中,在多少次激情洋溢的反法西斯主义集会上,听到人们说诸如“性格明显的”(charakterlich)特征,或者是民主的“战斗的”(kämpferisch)本质!这些表达来自于LTI的中心——第三帝国会说:“来自于本质中心”。我反感这些词语,是因为我迂腐吗?是我在这里暴露出了好为人师的本性吗?因为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每一个语言学者的内心都隐藏着一个指手画脚的教书先生?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通过第二个问题来加以澄清。
什么是希特勒之流最强大的宣传手段?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的一个个演讲?是他们对这个或者那个事物的阐述解说?或者是他们反犹、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蛊惑?
毫无疑问不是的。因为对于很多东西,大众都是懵懵懂懂、不知所云的,希特勒永无休止的重复也令他们丧失兴趣。在空袭期间,雅利安人有他们自己的房间,犹太人也要待在他们自己的屋子里,雅利安人的房间里有收音机(还有暖气和食物)——多少次,在旅店里(那时我还没有佩戴黄星,还可以出入旅店),后来又有多少次在工厂里,我都听见从隔壁房间传来扑克牌甩到桌面的声音,听到他们高声谈论关于肉和烟的配给、谈论电影,尽管领袖或者他的某个忠实党徒在那里长篇大论地讲话,而在这之后报纸则是宣称,全体人民倾听了他们的报告。
不,纳粹最强大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一个个演讲,也不是通过大量的文章或者传单、无数的标语牌或者旗帜实现的,它所依靠的,不是任何人必须有意识地思考或者有意识地感受才能够吸收接纳的东西。
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人们习惯于从纯美学的、平和无害的角度理解席勒的诗句“教养之语言,为你吟诗和思考”。而用一种“教养之语言”吟作一个成功的诗句,尚无以证明其创作者具有诗人的力量;用一种高度文明化了的语言赋予自己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神态,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然而,语言并非只为我吟诗和思考,它也导控着我的情感,驾驭着我的全部心灵,我越是想当然地、越是无意识地将自己交付给它,就越是如此。而假如这个教养之语言由毒性成分组成,或者是被制成毒性材料的载体了呢?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言说狂热,以为这就是英勇和道德,最终他就会真的相信,一个狂热分子是一位有道德的英雄,没有狂热的激情,就无法成为英雄。
词语“狂热”(fanatisch)和“狂热主义”(Fanatismus)不是第三帝国发明的,第三帝国只是改变了这些词语的价值,并且频繁地运用它们,其一天的使用率往往比其他时代一年的使用率还要高。第三帝国的语言里很少有自产自销的词语,也许、甚至基本上可以说根本没有。纳粹的语言很多时候都可以溯源到国外,其余部分里最主要的是从希特勒时代以前的德语里接收下来的。但是,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属于个别人或者一个极小的团体的东西变成了公众性的语汇,将从前一般的大众语汇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秘密的宣传蛊惑的手段。
揭示第三帝国语言的毒性,以此警示人们——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好为人师之举。怀有虔诚信仰的犹太人,当他们认为一件餐具已经沦为宗教意义上的不净之物时,他们便会把它埋入地下,以清洁之。我们应当将纳粹语言中的很多词语置入群葬墓坑,长时间掩埋,有一些要永远掩埋。
*本文选自[德]维克多·克莱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