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阅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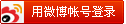
x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美国著名现代诗人,1879年10月2日 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市。大学时就读于哈佛,后在纽约法学院获法律学位。1904 年取得律师资格后,在康涅狄格州就业于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1934 年就任副总裁。在1955年,他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
文|罗伯特·勃莱 译|画皮
1
美洲大地上的文学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它的韵律依然涌动在埋于俄亥俄的大蛇身上(雅库特人吃过后扔在一边的蛇皮)。而美国的文学却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此间,那地下隐伏的黑暗究竟有多少已潜入了诗歌和小说?
所有的文学——古代的和现代的,都可以视作是受阴暗面驱使,重新从泥土中崛起并介入到光明的意识中的创造物。许多古代的宗教,尤其是那些信奉母教的宗教,通过强烈的感化来阻碍阴暗面进入人格。在那些神秘仪式中,这种对人的感化开始得很早,一直持续可达二三十年。在基督教中,(正如不少研究所揭示的,)曾经将人格分为阴暗人格和光明人格两极。基督教的道德常要受到阴暗人格的困扰。这种压抑愈益强烈,一个又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便落到了灵魂被割裂的境地,人格的两面已然相互迷失。我们秉有化身博士式的(参阅《The Strange Story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西方社会的典型人格,它倾向理智、怜悯、文明、纪律。一如杰基尔博士,他对病人关怀备至;而阴暗的一面却是残疾的,它行色匆匆,“就像一只猴子”,它比人格的另一面更为青春,蛮力十足而毫无道德。它“感应”着世代重压下的愤闷。
两种人格何以分离呢?我们以前面的二十或二十五年的生命,来判断该把哪些推入阴影品质,尔后的四十年又试图重新晤会这些元素。在对其所属的放逐上,各种文化表现各异。通常,我们可以把这“阴影”理解为所有我们身上的本能。它总是拖着一条尾巴,浑身毛茸茸的。世俗或清教文化中的人倾向于把性欲踩在脚下,并对死亡心存畏惧;他们常因此而迷狂。古老的洞穴匍伏在那儿,梦想着把整个世界一口吞下——如果我们陷入其中,那么露出地表的那部分便会显得无比体面。
康拉德是一位写作阴影文学的高手;《秘密的参与者》描述了对那种分离的整合(史蒂文斯却做不到)。康拉德常心存疑问:阴影不会重返意识,除非那人负有重大使命,比如,当一艘船的船长。
《阴暗的心脏》演绎了那种努力的失败。康拉德注意到:自从入侵非洲后,欧洲人极少致力于解决自身的阴影问题。在阴影的驱使下,现在的欧洲人执迷于金钱。库尔茨(《阴暗的心脏》中的主人公)的史学观认为,要一个白人在剥削黑人的同时克服自身的阴影,这不是人类所能做到的。
这种思考也萦绕在美国文学中——北方的和南方的。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芬恩》中精彩地表现了相似的主题。有时在美国,“正派人”被藏匿在阴影里,和其他许多东西相混。正如哈克贝利·芬恩发现的那样,只有当你拒绝出卖吉姆时,“正派人”才会复归于你。
我们的大多数文学试图描写阴影的兴起,以及阴影的失落。不知为何,亚哈(Ahab)失败了;他秉有很强的自制力,满腹希伯莱先知诤诤有词的“旧道德”。狄美斯多(Dimmesdale)的阴影败落了。显然是他对女人的畏惧阻碍了自身阴影的兴起。我之所以用“阴影”而不用“邪恶”来谈论文学,是因“邪恶”总是能量十足,好似某种外在于我们的强有力的存在。“阴影”却是笨拙的,但它显明了那些内在于我们自身的能量。
A.大卫-奈耳(Alexandra David-Neel)讲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故事。本世纪初当她跟随几个西藏导师研修时,他们建议她试着去获得有关生命力或称力比多(libido)的更为清晰的体验。他们建议她要把它放在自身之外来对待,这样她才能看得更清楚,而不受制于客体;由此,进入一种思维状态,幻见一个头脑之外并不实在的图像。她决定不选用典型的西藏幻象——几个精壮的舞者形象,戴着头盖骨串成的项圈,胸毛闪闪发光——当时她可能以为那只是西藏人无意识的一种简单转化。最后她决定幻觉一个中世纪的英国修士。经过几周的幻觉(其间她做了另外一些功课),有一天当走在修道院外的路上,她注意到一个灰色衣着的英国修士从她身边走过。几次相遇后,他开始在见面时向她致意,这时她能看见他的双眼。如果她停止冥想,他便会消隐。可是不久,她发现他变得越来越猖狂了,他忤逆她的意旨,强行出现以攫取她的能量,并开始张扬他自已的生命。这下,她畏惧了。最后她到她的西藏导师那儿求助,那位导师教她如何举行一种冗长的仪式以摆脱那个修士。如果某个男人(或女人)在谈论《白鲸》中的邪恶,那么他(或她)就是那种人——相信那修士是真的。
2
1875年至1890年间出生的一组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弗罗斯特、艾略特、威廉斯、M.摩尔、庞德,以及杰弗斯,他们全都是阴影诗人。他们不仅仅是些阴影诗人,但他们着实写了不少的阴影作品。从上世纪末开始,大部分阴影作品出现在小说中;而在本世纪却趋向于在诗歌中显现。史蒂文斯通常被认为不是一个阴影作家,所以我们有必要选择他来讨论;而他的作品却成为那个奇异组合的杰出代表。
把K.雷克斯罗思(Kenneth Rexroth)自传中的K.雷克斯罗思和史蒂文斯作一个对照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雷克斯罗思一家试图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外。史蒂文斯的家庭(中产阶级上层德裔美国人)显示出对阴暗面的可敬的忍耐力。我不清楚阴影是如何复归于个像史蒂文斯那样复杂的人的;对此我真是一无所知,而在这里我所说的只不过是些臆测。但可以想见的是,阴影的能量若要复归必得有特殊的渠道。艾略特强烈的感伤,先是来自他的婚姻,接着是他妻子的精神错乱,这些都相应地提升了许多阴影能量。而史蒂文斯根本没有这么深重的苦闷。对于史蒂文斯,阴影在绝对平静的状态中兴起,伴随着感官的觉醒,特别是听觉和嗅觉。正是感觉,在我们和动物性的过去以及阴影间架起了天然的桥梁。嗅觉,阴影以及黑暗,对色彩和声音的认知,这些存在于先人身上,意味着生与死。同样,它们也存在于我们身上,不过已经麻木了。它们麻木于闲适,麻木于长期的校园生活。史蒂文斯似乎在他供职于保险公司的早期,总是在几个新英格兰城镇的博物馆里结束他的一天,他花上一二个小时观赏那些画。这是一种唤醒感官的措施,就像行走一样。这两种方式比阅读能唤醒更多的感觉。
在十二座披雪的山间, 那惟一活动的 是黑鸟的眼睛。
据说,西方读者为此感到强烈的反差;其他的感觉全都淡化了,阅读的重心侧向了视觉。五种感觉间那种古老的和谐被摧毁了。史蒂文斯凝神细听:
我不知道我更喜欢什么, 那变音的华丽 还是那影射的精妙, 那黑鸟的鸣啭 还是鸣啭后的寂静。
……
整个下午一如黄昏, 它下着雪 它还将下个不停。 黑鸟栖息 在那雪松枝头。
最后一节诗人以绝妙的、敏锐的笔触感念了光的变化,渐渐深化的黑暗,以肉体来感应那将临飞雪。他与众不同地以更多的注意力来整合对色彩和气味的感觉。
那一个女子的 手臂颜色的夜晚; 夜晚,女人, 晦涩, 芳香而柔顺 藏起她自己。 水池闪烁, 如同一只手镯 闪耀在舞蹈中。
他以眼睛去感触:
那光如同一只蜘蛛…… 你眼中的蛛网 被紧紧地拉向 你的肌肉和骨骼 仿佛那是房椽或草丛。
你眼睛的细丝 在水面上 在雪的边线里
他着手谈论天气,且寓情于其中:
雨的激情,落雪里的思绪; 孤独中的悲愁,无法克制的 林木开花的喜悦;汹涌的 秋夜湿路上的情感;
他开始观察——设若感觉因劳作而变得敏锐——你如何伴着围绕你的造物和客体而显露:
我是那围绕我的一切。
女人懂得这个, 离开马车一百码 她便不是公爵夫人。
一旦他流溢出感觉的光芒,奇异而神秘的内容就从诗中升起:
他穿过康涅狄格 驾着一辆玻璃马车。 一次,恐惧刺中了他, 因他误把 马车的阴影 当作是黑鸟。
这里展示了一个纯粹的阴影例子,从中阴影原素喷进了意识层。通常,喷进意识的阴影只要持续那么一瞬,就能给我们带来毁灭感。奇怪的是,有时候凝神于蚂蚁也能招致相似的后果:
以一棵大树 我丈量我自己。 我发现我高出了许多, 因我以我的眼睛 触到了高处的太阳; 因我以我的耳朵 听到了远处的海岸。 只是,我不喜欢 那蚂蚁爬行的方式 它们进进出出在我的阴影里。
我猜想那些以译诗阅读史蒂文斯的人很难体会到:阴影无比体面地渗入感觉。因为他在诗中流露的那种杰出的感觉才能,仿佛是某种萦绕着英语词汇的神韵;就像有一种香气萦绕着每一种金属、每一棵树。而在英语中长大的读者,他们对语言的悟性已经被泛滥的报纸败坏,也许也不能领略到史蒂文斯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神韵。
凭着光,那咸涩的鱼 弓身在大海里,一如树枝, 游走在不同的方向 忽上忽下
各种感觉交叉在这些诗句中。它不同于学院诗或者哲学措词。
这会更好,就像那些学者 他们会苦思冥想 在大氅的黑暗袖口里……
当芭蕉(Basho)在花园中听到寺庙里的钟声,他写道:
寺钟不再震荡―― 但那声音却萦绕不去 在那些花上。
芭蕉以佛教徒和俳句诗人的双重身份来唤醒感官:
大海暗了。 无边黄昏的声息 渐渐泛白。
美国的俳句诗人没有领会到,阴影必须升起并侵入诗歌,否则那便不是一首俳句。至于它的十七个音节,或者所写的自然风光,都是无关宏旨的。
史蒂文斯提及并徒然地试图用作自己一本诗集的题目的“风琴”,实指五种感觉的联姻,也许不只五种,甚或有八九种之多。恐怕只有澳洲的猎手或是芭蕉才能辨别得出来。冷静赋予史蒂文斯的诗行一种音乐性,大有古人综合各种感觉时体现出的那种风范。最近,我饶有兴趣地发现了使他的诗歌达到那种效果的主要帮助者,他就是W.詹姆斯(William James)。我们通常认为感觉和思考是相对立的,因此我们判定,如果某人要想唤醒感觉,那么他必须停止思考。当我第一次读到《风琴》,我惊诧于作品是通过声音和气味来表达思想的,随着思想的深入,感官的想象也被强化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种思考方式是受W.詹姆斯启发的。M.彼得森(Margaret Peterson)在《南方评论》(1971年夏)一篇有关史蒂文斯的文章中,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一点。它指出《风琴》中几首最晦涩的绝妙的诗歌,其实是对詹姆斯的一些篇章的转述。多么叫人吃惊!
W.詹姆斯提醒他的学生,有一种思想倾向贴近西方——它几乎称不上是一种思想方法——这种倾向无视事物的细节。无视手指甲,复数的树林被关注,而没有一棵独特的树木被人迷恋过,无论它身处何方;耳中的细毛也被忽视了。我们发现这种倾向充斥于年轻人的英语论文里,美国学生驾轻就熟地写些空洞无物的问题;名词通常用复数形式,而其中的感想最好是具普遍性的。同样的思想也出现在水门事件的那些磁带上,而现在普及得更广,英国毕业的研究生,把叶芝诗中所有的细节归纳成“典范”或什么“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这就好像用佛兰卡语(lingua franca:意大利混杂语)取代拉丁语。这种倾向可以形象地被描述成一种不用联想到狒狒耳中的细毛甚至整个的一只狒狒,而对非洲高谈阔论的本事。相反,这种倾向会谈论“野生动物”,因为无穷的色彩归根结蒂全都属于大宇宙,它是不会在意色彩的。拥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就像拥有一件千篇一律的白色睡衣。因为对他们来说,3与742是没有什么区别可言的;某物的多少只不过是一个细节而已。正如詹姆斯所说,其实他们只对一个数字感兴趣,那就是1,它不带具体的细节。在阅读彼得森的文章时,我惊奇地发现《某个贵族的隐喻》——一首我曾喜欢,并以为是对崇高理念的戏仿的诗,居然成了一首严肃的精心制作的诗歌。这首诗提示你,该如何摆脱那种思想倾向;如何避免被它谋杀。(由此可见,哲学博士对《风琴》的解析实在是可笑。)他写道:
二十个人过一座桥, 进一个村庄, 是二十个人经过二十座桥, 进二十个村庄, 或是一个人 过一座桥进了一个村庄。
他清楚自己是以参与政府计划的哲学博士候选人、政客和专家咕哝着哼出的那种悲伤小调起笔的:“此与彼等量齐观。”
这是老调 它不言而喻……
接着他指明了该怎么做。停止那些思想的小把戏。身临其境,以你的躯体,让感觉为你开路。先是声音,接着是视觉,如果可能的话,再加以嗅觉。向你的想象力征求声音:
人群的一双双靴子 落在桥板上。 那村庄的第一堵白墙 从果林中升起。 我正想些什么? 意义就这样溜走了。
那村庄的第一堵白墙…… 那果树林……
多么怪诞!这竟是一首指明道路的忏悔诗,是某种宗教诗。却又是如此的优美!
W.詹姆斯发现了这种思想倾向并相应地提供了许多例证。他注意到这种思想倾向类似于波士顿的上层阶级。他们嫌恶污浊的细节——宗教耳孔里的毛,散发着爱尔兰道口的气味——而喜爱“一”的宗教。于是,他们便成了一神论者。如果某个文化人沾染上了这种思想倾向,那么一桩严重的事情发生了:生活的上半部分(精神的)和下半部分(感官的)开始了分离。一半上升了,而另一半失去了和高处的联络,沉落了。二者之间的沟壑变得越来越宽。知识阶层拥有纯净的那一半,而工人阶级一无所有,除了他们粗俗的形而下的生活琐碎——丈夫衰老的嗓子以及咳出的痰液,浴缸,门口地板上孩子的靴子带来的水和未化的雪,脚上的玉米粒,浸泡着的杂乱的碟子,寒冷卧室里世俗的欢爱。这些形而下的琐碎遍布二十世纪,不仅未被宗教渗透,而且在潜意识里抗辩“宗教是无用的”。詹姆斯强调这种认识,而史蒂文斯一生感伤于这种觉悟。工人阶级一无所有除了“冰淇淋皇帝”。如今的中层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所以说,如今大部分西方人活得比中世纪还糟。
詹姆斯还注意到这种思想倾向在印度的表现,并且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吠檀多哲学(Vedanta)是叫人乏味的。一个和安纳达·玛迦(Ananda Marga)共事的印度冥想师最近告诉我,在他完全独立地进行冥想之前,当时他正在印度的一家压缩机厂做工程师,晚上他要去走访由镇上的圣人主持的晚会。演讲结束后,他问在场的听众:你和印度穷人的关系是什么?通常——我想他是说经常——十多次发生了争执——两个干瘪的人会过来将他带出大厅。史蒂文斯自然会懂得其中的道理。对大多数印度圣人来说,穷人便是印度耳孔里的毛。他们崇尚“一”,它没有毛。
詹姆斯还使他的学生相信第三个例证,他罗列了和这种思想倾向相关的德国理想主义者。他们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是布雷德莱(Bradley),在美国是J.罗伊斯(Josian Royce)和“盎格鲁-黑格尔信徒”(Anglo-Hegelians)——可怕的典范,“一”的专家,中层阶级城堡以及上层阶级候客厅的建筑者,乏味的授奖词和耸人听闻的末世图的写作者,实在比蒲伯·保罗(Pope Paul)还差劲,他们就像一些灰色瓦罐,如果放得进,他们将摧毁整个田纳西那样的州;人们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的立足地——他们可以长年居住在一个山谷而从不属于它。一直致力于哲学研究的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对他们也有描述:
我去过见过的一个个地方 伤感的一次次远足, 愤怒而忧郁的 拖着黑色影子的酒徒,
而幕后的学者 他们瞧着,一声不吭,想着 他们的知识,因为他们不在普通酒吧 啜饮酒浆
邪恶之徒大步流星 污染着大地……
马查多还写道:
人类获有四件 不利于航海的东西: 锚、舵、桨, 以及对下沉的恐惧。
如果我们以荣格(Jung)对阴影所作的分析来思考理想主义,那么,我们便会清楚地发现,理想主义者是些不愿往下走的男女。他们打算压着阴影一直走向坟墓。理想主义者都是些憎恶阴影的人。他们都和杰基尔博士有同样的结局,有一个猴子样的海德先生在城市阴暗的建筑群中行色匆匆。
对“真理”情有独钟,他们放逐阴影,或者维护对它的放逐…………当史蒂文斯和所有这一切针锋相对的时候,他同时也在反对完美的天堂,反对抽象的教堂,反对统计学似的智性,反对太轻松的玄虚,和太轻松的对悲剧的忽略。
不完美是我们的天堂。 记下它,在悲愁中,在欢乐中, 那不完美如此炽烈地内在于我们。 在残破的语词和执拗的声调里。
史蒂文斯没有重蹈狄美斯多的覆辙。他吸收阴性的事物进入他的诗歌;佛罗里达,月亮,牵牛花和珊瑚,泽地船,阔边帽,脚下的鞋底和葡萄叶,卡罗兰纳的小屋,还有各种各样的音响!
唯有阴影才深谙音响的魔力。当一听见酣畅而又原始的文森延音乐(Vincentine),(像莫扎特一样饱满,像澳大利亚鼓一样坚定。)你就能体会到阴影的一部分已经找到了返回的途径:
是的:你款步而来, 文森延 是的:你言说着前来。
而你对我所知的感应 随后而来。 我眼中单调的世界 因你而变得无垠, 而那苍白的走兽,如此疲乏 归向文森延, 归向极乐的文森延, 而那苍白的走兽,如此疲乏, 归向极乐的,极乐的文森延。
这样,史蒂文斯寻到了返乡之路。他认识到那些信奉基督的希伯莱理想主义者,他们强调存在着一个绝对真理,它要求我们时刻扼制阴影的兴起,因为凭着一个人脆弱的心智,很容易动摇或者自暴自弃。他写了那首明晰而又优美的诗——《返乡之路》:
当我说道: “根本没有那样的真理,” 那葡萄就变得丰盈。 那狐狸就奔出洞穴。
你……你说: “有许多真理 但它们并不归向一个真理。” 于是那树,在夜里,开始改变,
吸吮过绿色,又吸吮着蓝色。 我们是林中的两尊雕像。 我们孤立着絮语。
当我说道: “词汇并非单个词的变形。 个别的总和里,依然只有个别。 世界须由眼睛来丈量”;
当你说道: “偶像见过种种贫穷, 蛇,金子与寄生虫, 却没见过真理的贫穷”;
正是这一刻,寂静无边无际 而且漫长,夜,无比的圆满, 那秋的芬芳最最温暖, 亲切而浓郁。
3
创作了《风琴》那样的杰作之后,受到詹姆斯书中的那些神秘启示的导引,史蒂文斯陷入了困境——他清楚他的困境——为何故事就此枯竭了?
有时我们追寻故事的结局 那里本该有盛大的婚宴, 却只看见,一切如旧, 黑金盏花和一片寂静
评论家常会接受诗人创造的世界。如果诗人把“东”说成“西”,他们便说:我以前怎么没想到?
所以史蒂文斯的评论家们全都热衷于阐述他作品的种种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诗歌几乎是一个天才可能写下的最平庸的作品;更为糟糕的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藏有“白色睡衣”式的心智。
虽然还有若干首好诗,但他的作品再也没有婚宴了。叶芝作品却源源不断地纳入越来越多的细节,感觉的阴影也随之而起,本能之力丢开了它的小丑服,倾注入越来越丰富的意识。
这种情况为何没在史蒂文斯身上发生,这我拿不准,但是我认为有必要观照一下他的生活。勃姆(Boehme)在他的一本前言中,敬请读者不要走得太远,要单纯地读书,而不要奢望借此达到某种现实性的转机。不然,勃姆警告说,读书将是有害的,危险的。我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和阴影的关系已在美国艺术家中树立了某种典范:他把阴影引入他的艺术,但又保持自己的生活一尘不变。欧洲的艺术家——至少叶芝、托尔斯泰、高更、凡高、里尔克他们——似乎更懂得,阴影必须生存,就像在艺术作品中被接受那样。他们所有艺术的旨趣在于,一个男人(或女人)成功地以感觉写下丰满而又鲜活的诗行那一刻,而这一刻充满阴暗,比如下面的诗句:
鹌鹑 以他们固有的哭腔向我们尖叫
他必然因此而改变他的生活。仿佛是对他的语言转机的一种回应,他的生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当里尔克的作品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我们发现,里尔克随时会听从艺术的指令而着手去改变他的生活道路。一天,他久久地注视一尊雕像,这尊古老的雕像为一群狂热的阿波罗崇拜者围绕,他看到这形象不仅头部栩栩如生,而且躯体的任何一部分都光彩照人,那光彩遍布胸腹,一直导向生殖器:每一局部都在凝视你,他说。于是,他下定决心在明天到临之前必须对自己的生活作出某些改变。由此我想起那些大学教师,他们因为叶芝在二十几岁时写的一篇日记里的话而嘲笑他,那句话的大意是:我的韵律变得越来越松驰了;我想我最好在一张桌子上躺一会儿。但这说的恰恰和里尔克的诗歌如出一辙。
华莱士·史蒂文斯无意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尽管他得到了不少来自阴影的馈赠,尽管从自己的诗歌中也读到了不少启示。他却始终恪守家居的整洁,死板地在一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睡了三四十年。以静若止水的心绪过他的生活,并且严守职业生活和诗人生活的分离——所有这一切,使他在日常生活中确保了他的主人格不和阴影人格相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他领着一位文学来访者到他的俱乐部用餐,史蒂文斯俨然像一个商人那样交谈,并且提醒来访者不要有出格的举动。1935年,墨索里尼攻打埃塞俄比亚,当时56岁的史蒂文斯在给R.拉提美尔(Ronald Latimer)的一封信中称:
就像那些黑鬼从大蟒手中获取埃塞俄比亚那样,意大利人有充分的理由从黑鬼手中获取埃塞俄比亚。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句戏言,并不表明他因此有罪。但这一句话,那些热爱史蒂文斯诗歌的读者迟早总要面对。它似乎可以向我们说明,他并无太多的激情实现他的阴影。他力促阴影进入《风琴》,但当这些阴影有可能干扰他未来生活的进程,或内心的主张开始迎合这些阴影时,他便猛然将那扇门关上。
我知道以关注作家生活细节的方式来对一组诗歌作出严肃的批评,这有悖任何一条极富影响力的新批评的准则。但我们现在必须看到,新批评坚持的只对作品作分析,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W.詹姆斯和史蒂文斯他们对那种思想倾向的警惕被抛弃了,到了四十年代,理想主义就在文学中站稳了脚跟,四五十年代开始创作的我们全都能敏感到这个事实。批评家们想当然地将诗人和诗歌割裂开来。艾略特为这种观念推波助澜,但大约1957年在圣保罗的一个曲棍球场,我亲耳听到他抱怨他的诗不久前被印在一本收有八首长诗的集子里,而该诗集对创作这些诗的作者只字未提——他们没有国藉,没有生活的年代。“除了我,他们都已作古,一打开书本就让我感到自己死气沉沉。”那位编选者的观念正是史蒂文斯所说的“白色睡衣”式的。无论如何,到了五十年代理想主义已在文学批评中安营扎寨,而在如何将自身的阴影或者民族的阴影引入我们的诗歌方面,它对我们这些后来的创作者毫无助益。
华莱士·史蒂文斯在俱乐部的形象——不太谈论诗歌,或谈得不太有激情——完全和托尔斯泰相反。当步入老年,托尔斯泰打算给他的农奴以自由,他一意孤行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还以为这些农奴是财产和嫁妆的一部分时一切都已丧尽。托尔斯泰携着他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在一场暴风雪中离开了家园,不久死在了一个火车站里。这么晚了他还是想望能改变他的生活道路!
这故事也许是一个蛮糟糕的例子,因为它暗示了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会造成严重后果,大难临头,极度不安,离开妻儿,离开丈夫,以易卜生的姿态将门重重地关在身后。这些负效应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巨大的改变——离婚,舍下孩子,抛弃责任,似乎是重返阴影最直接的途径,可是奇怪的是,多数情况下这样仍无济于事。当某人离了婚,他(或她)往往随即又和另一个人组成了相似的生活。以往岁月中,诗人和读者共同经历的,所有忏悔诗的词语风暴并没有为诗人成就任何东西——忏悔书虽已写就,诗人的阴影仍然相隔遥远。普拉斯(Plath)、塞克斯顿(Sexton)和贝里曼(Berryman)他们的生活是些明证,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死亡冲动依然企望着向分裂的灵魂猛扑。
显然,里尔克所说的“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是意味深长的。我自己也不甚明了,因此我只能臆测。康拉德显然利用了阴影提供的素材,当他结束了在刚果的船长生涯(这样一个非洲的小剥削者)。里尔克,当他在创作中受到启示,他会中断他的诗歌写作,花上几个月去观察动物园里的动物和街头的盲人,甚至承受长年的孤独。他对人世的所求越来越少,而不是更多。道教徒也许认为改变生活道路意味着出世。趋向“无为”,不充当任何尘世的角色。王维被认为是淡泊无为的。他曾写道:
古人非傲吏, 自阙经世务。 偶寄一微官, 婆娑数株树。
他的挚友裴迪和道:
好闲早成性, 果此谐宿诺。 今日漆园游, 还同庄叟乐。
人对世界的介入主要通过一些社会习俗。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人的后半生他有必要摆脱习俗的羁绊。我觉得这个问题对女性显得尤为棘手,但个中原因我不甚明了。可以想见,那样的改变会给女性招致诸多的责任问题。
无论如何,在美国并无“出世”的传统,这儿的人一般会在习俗中越陷越深,当他四五十岁时,他会在一家保险公司或是一所大学里安居乐业。约翰·巴思(John Barth)是美国艺术家中试图将阴影置入他的创作,却拒绝使它存活的一个当代典型。他的创作不得不重蹈史蒂文斯的覆辙——它升向虚空,执迷于智力的芜杂,从枯燥的理念之府引出对枯燥理念的反省。
如果阴影的馈赠没被付诸实践,那么它最终会退隐并返回泥土。阴影给予写作者(或某人)十至十五年的时间去改变他的生活,以回应它为他带来的瑰丽的幻象——这种改变也许只导致男女内在的两性婚姻的深化——但如果转机没有发生,那么阴影便会弃他而去,而那人的景况便大不如前了。里尔克在下面的这首诗中谈到了阴影的退隐。
成熟的伏牛花已然嫣红, 而衰老的紫苑残喘于它们的花床。 夏日已尽,而今仍未茂盛的人 他将终日苦等,且永无归所。
那无法静静瞑目的人 坚信内在的幻象会接踵而来, 呆呆地守候,直到黑夜 将周遭的幽暗全然升起—— 他是老人,他已走到了尽头。
再没有来者;再没有开放的时日; 一切发生都将伤害他—— 甚至您,我的主啊。您犹如石头 让他一天比一天陷得更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