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阅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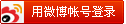
x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化学家,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他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第174517号囚犯,也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写作了“奥斯维辛三部曲”(《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备受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卡尔维诺、安伯托·艾柯等文学大师推崇。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序言 ——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录 文|普里莫·莱维 译|杨晨光
在1942年这个关键的年头,关于纳粹进行种族灭绝的消息开始流传开来。虽然只是些模糊的只言片语,但这些消息相互印证,勾勒出一场大规模屠杀的轮廓。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残忍,如此错综复杂的动机,如此罪大恶极的罪行,人们往往难以相信它们的真实性。有意思的是,这些罪犯早已料到了公众们的质疑:许多幸存者,如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在他的著作《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结尾处回忆党卫军喜欢用嘲笑的口吻训诫囚犯: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做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他们会说这是盟军的夸大宣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非常奇怪,出于绝望,同样的想法(“即使我们把这些事情讲出去,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也会以梦魇的形式出现在囚犯们的脑海中。几乎所有的囚犯,在他们的口述或回忆录中,都会记得在集中营常做的一个梦。梦的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回到家,带着热情和宽慰,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但对方不相信,甚至不倾听他们的讲述。在最典型(也是最残酷)的梦中,对方会默默转身离开。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话题。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受害者,还是迫害者,都怎样深刻地意识到集中营所发生的滔天罪行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在此我们还要补充的是,这些罪行不仅发生在集中营里,也发生在犹太人隔离区,发生在东部战线后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里。
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以受害者所担心的(也是纳粹所希望的)方式发展。即使最完美的组织也有弱点。而希特勒的德国,尤其在崩溃前的几个月中,远远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大量关于大屠杀的物证被销毁,或者多多少少被巧妙地尝试去销毁证据:在1944年秋天,纳粹炸毁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但废墟仍然在那里。不管纳粹的追随者们如何歪曲事实,他们都难以借助千奇百怪的假设为它们提出合理的用途。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在1943年春天那场著名的起义后被夷为平地。但多亏众多战士(他们既是战士,又是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的非凡努力,证据被保留下来——在瓦砾堆中,常常在数米之下,或被偷运出高墙之外。使其他历史学家后来能够重新发现这些证据,从而了解隔离区内每天的生活和死亡。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所有集中营档案都被烧毁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受害者的人数是400万、600万,还是800万——但仍以百万为单位。在纳粹修建起的一座座巨大的焚尸炉前,无数遇难者的尸体,被蓄意杀害的,在苦难和疾病中殉难的,可能成为大屠杀证据的,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消失。最初的措施,可怖到让人难以启齿,是把尸体,成千上万的尸体,草草地堆积埋葬在巨大的万人坑中。这样的措施真的被付诸实施了,尤其是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其他小型集中营,以及德军侵略苏联之时。这是一种野兽般漫不经心的临时措施。那时德军在各条战线节节获胜,最终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他们可以在胜利后再决定怎么办——毕竟,胜利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连历史真相都可以随意书写。无论如何,可以为万人坑诡辩,可以让它们消失,也可以把黑锅扣到苏联人头上(在这方面,苏联人在卡廷惨案中证明他们并不比德国人差多少)。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人改变了主意——最好马上销毁所有证据。集中营的囚犯们被迫挖出那些可怜的遗骸,堆在空地的柴堆上烧成灰烬,似乎人们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些反常的大规模行动。
随后,党卫军指挥机构和安全部门殚精竭虑以确保消灭所有证人。这正是他们在1945年1月间,草菅人命而丧心病狂地转移集中营囚犯的用意所在(难以有其他解释)——随着囚犯被转移,纳粹集中营的历史也得以篡改:麦达内克(Maidanek)的幸存者到奥斯维辛,奥斯维辛的囚犯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到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的女犯们到什未林(Schwerin)。总之,当德国人在东西两线频频败退之时,他们必须攫走每个迎向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转移向德国的核心地带。纳粹并不在乎囚犯们可能在转移途中倒毙,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事实上,从作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为死亡工厂,再(或者同时)成为巨大的、不断更新奴工苦力的劳动营,集中营已经对行将灭亡的德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集中营的秘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了解大屠杀真相的犯人们,德语称为“Geheimnisträger”,组成了仍然植根于集中营的幽灵军团,必须加以处理。已经被拆毁的灭绝营,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不得不向德国内地转移。这些决定,一方面是荒唐地希望减少不断逼近的前线对集中营的威胁,继续把这些“幽灵”困锁在集中营内,进一步压榨他们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恶毒地希望如《出埃及记》 般行军的苦难折磨会减少他们的人数。而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的确惊人地减少了,可一些囚犯靠着运气和体力活了下来,成为大屠杀的证人。
鲜为人知(也少有人研究)的事实是,在德国人中,仍有很多人掌握着大屠杀的秘密,尽管多数人了解得不多,但个别人却深谙一切。永远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出,在纳粹机构中,有多少人会不了解纳粹所犯下的可怕暴行;有多少人了解一些真相,却装作毫不知情;还有多少人原本可以了解其中的所有真相,却更谨慎地选择闭目塞听(更是缄口不言)。无论如何,即使我们不能假设大多数德国人轻松愉快地接受了大屠杀,但可以肯定的是,隐瞒集中营的事实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又一项重大集体犯罪,并极为显然地证明了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经使德国人民归于怯懦。这种怯懦,已经成为德国人行为习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让丈夫无法向妻子讲述真相,无法对子女进行教育。没有这份怯懦,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今天的世界和欧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那些成为(或曾经成为)纳粹帮凶而了解可怕真相的人们,无疑有着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不过,既然他们掌握着秘密,即使沉默也无法确保他们的性命无虞。就像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特拉夫尼基” ,他们见证了斯坦格尔以及其他刽子手的罪行。但在纳粹镇压了特雷布林卡的囚犯暴动并拆除了这个灭绝营之后,他们却被遣送到了最危险的游击区之一。
许多见证了集中营暴行的“平民”们,作为潜在的见证者,因为有意地忽视和恐惧,同样保持缄默。尤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集中营所构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广泛地渗透到德国的日常生活中,正像人们所说的“集中营世界”(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但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农业合作社、代理商和军工厂借助集中营提供的免费劳力渔利。一些企业无情地压榨囚犯的劳动价值,接受党卫军冷酷(而愚蠢)的原则——一个囚犯和另一个囚犯的价值相等,要是累死了一个囚犯,马上就会有另一个囚犯替换上去。少数企业小心翼翼地尝试减轻囚犯们遭受的折磨。另一些企业(也可能是同一些企业)通过供应集中营木材、建筑材料、犯人穿的条纹囚服、做汤用的脱水蔬菜,等等而获利。一家德国公司,威斯巴登的托普弗公司(Topf of Wiesbaden)设计、建造、组装和测试了集中营使用的焚尸炉(这家企业在1975年仍在营业,生产民用焚尸炉,仍未考虑过改名)。很难相信这些企业的员工们从未意识到党卫军指挥机关订购的这些机械设备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重大意义。同样的质疑也适应用于奥斯维辛使用的毒气:氢氰酸。这项产品多年来在船舶养护中一直用于寄生虫的防治。但从1942年起,突然大幅度提高订量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无疑曾引发人们的猜疑,但恐惧、对效益的渴望、我们提到的盲目和装糊涂,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很少)对纳粹的疯狂服从,压制了人们的质疑。
显而易见,在了解集中营的事实时,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们的回忆。但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集中营并不总是一个好的观察对象:在非人的条件下,囚犯们的观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对生活环境构建一个笼统的印象。囚犯们,特别是那些听不懂德语的囚犯,坐在闷罐车厢里,经过一段充满折磨的致命旅程之后,可能甚至不知道他们的集中营位于欧洲的什么位置。他们不知道其他集中营的存在,哪怕仅在几公里之外;不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也不知道生活条件的突然改变或大规模转移的重大含义。被死亡环绕着,这些被放逐者根本无法了解眼前这场屠杀的规模。今天还在身边工作的伙伴,明天就消失了,也许在隔壁的棚屋里,也许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抹去,无从知晓。总之,囚犯感到被一种巨大的暴力和威胁体系所淹没,而自身却无法对其做出表达或刻画,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注意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这个缺陷制约了“普通”囚犯的证词,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那些没有特权的囚犯,代表着集中营的核心。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才让他们逃脱了死亡的命运。他们是集中营里的大多数,却是幸存者中的极少数——在幸存者中,在集中营里享有某种特权的人数要多得多。多年之后,今天的人们可以更明确地肯定: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就像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低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低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
另一方面,“特权阶级”的见证者本身无疑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只因为他们站得更高,有着更广阔的视野。但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关于特权(不仅在集中营里)的讨论是微妙的,但我仍会在本书中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要提出一个事实,那些地位最高的“特权阶级”,也就是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做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所以,最好的集中营历史学家出自极少数人之中——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因为与犹太人和其他囚犯(正如我们知道的,集中营的三大类囚犯)相比,政治犯拥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因为,更准确地说,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因为他们更易于接触到统计数据;而最后,因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着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至少,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允许他们记录和保存笔记,这对于犹太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而其他囚犯们则可能毫无兴趣。 | 


